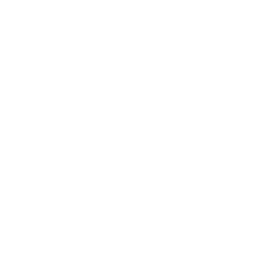第41章
“嘎吱——”
刺目的光线如同利剑,瞬间劈开了衣柜内部粘稠的黑暗!
蜷缩在角落、几乎与阴影融为一体的张伟强,被这突如其来的强光狠狠刺中,布满血丝的眼球猛地一缩,爆发出难以忍受的刺痛。
他像一只被强光照射的蟑螂,惊恐地、条件反射般猛地向后缩去,后背重重撞在挂满衣物的柜壁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咚”响!
浑浊、令人作呕的空气如同实质般扑面而来——浓烈的汗酸味、灰尘的呛人气味,以及……一股浓重到化不开的、属于他自己精液干涸发硬后散发出的、如同变质鱼腥混合着铁锈的浓烈腥膻恶臭!
这气味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
顾晚秋站在敞开的衣柜门前,清晨的光线毫无保留地勾勒出她赤裸的、成熟丰腴的胴体。
肌肤上布满了昨夜疯狂的证据:从颈侧到胸乳的深红吻痕,腰臀处清晰的指印,尤其那浑圆挺翘的雪白臀瓣上,还残留着几道被用力拍打揉捏后留下的、尚未完全消退的淡红掌痕。
她微微蹙起秀气的眉头,不是羞涩,而是毫不掩饰的、极度的厌恶和鄙夷。
她的目光如同冰冷的探照灯,扫过衣柜内部——散落一地的衣物被踩踏得不成样子,深色布料上溅满了干涸发黄、如同污渍地图般的精液斑块,柜壁的木板上也沾染着点点污秽,甚至他蜷缩的那个角落,地面都凝结着一片深色的、散发着恶臭的粘腻。
最终,她的视线定格在张伟强身上。
他眼窝深陷,脸色惨白中透着一股濒死的潮红,头发油腻打绺,胡茬杂乱,身上那件皱巴巴的衬衫和裤子同样沾满了灰尘和干涸发硬的污迹,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行将就木的、垃圾般的腐朽气息。
顾晚秋的眼神冰冷如万年寒冰,充满了赤裸裸的轻蔑和胜利者的睥睨,仿佛在审视一堆散发着恶臭、亟待清理的秽物。
更刺目的是,她因站立的姿势和昨夜今晨的激烈性爱,下体那微微红肿、如同熟透花瓣般无法完全闭合的穴口,正缓缓地、不受控制地滴落下一缕粘稠的、混合着滑腻爱液和儿子新鲜精液的浊白液体。
那液体拉出细长的银丝,在晨光下反射着淫靡的光泽,最终“滴答”一声,精准地砸落在她光洁的脚踝旁、冰冷的地板瓷砖上,留下一点新鲜的、刺目的污迹。
张伟强的目光,如同被磁石吸住,死死钉在那滴落的、象征着妻子被儿子彻底占有和征服的液体上,巨大的屈辱和绝望如同冰冷的毒液瞬间灌满四肢百骸,几乎将他撕裂。
他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干裂起皮,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风箱般的艰难喘息。
他挣扎着,用尽全身仅存的力气,努力抬起头,布满血丝、充满惊恐和卑微乞求的眼睛望向顾晚秋,声音嘶哑破碎得如同砂纸摩擦粗糙的木头:
“老…老婆…”这个称呼出口的瞬间,他自己都感到一阵荒谬的刺痛,“我…我的病…好了…真的…可以…不用治了…”他艰难地挤出这句话,眼神里带着最后一丝如同风中残烛般的希冀,乞求着这“治疗成功”能成为他留下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能挽回一丝早已荡然无存的尊严。
顾晚秋闻言,嘴角那抹冰冷的弧度骤然加深,化作一个充满极致嘲讽的嗤笑,如同冰锥刺破空气。
她的目光如同最精准的手术刀,刻意地、缓慢地下移,最终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落在了张伟强裤裆处——那里一片死寂的萎靡,裤裆布料松垮地塌陷着,与他儿子那根即使在沉睡中也依旧彰显着惊人存在感的雄风,形成了地狱与天堂般残酷的对比。
她收回目光,重新直视张伟强那双写满惊恐和卑微乞求的眼睛,声音清晰、冰冷、不带一丝人类的情感波动,如同法官在宣读最终的、不容上诉的死刑判决:
“首先,”她竖起一根纤细却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的食指,指尖在晨光下泛着冷玉般的光泽,“这个‘治疗方案’,”她刻意加重了这四个字的读音,带着浓浓的讽刺,“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地强调着“你自己”这三个字。
“但是,”第二根手指如同冰冷的铡刀般竖起,眼神锐利如淬毒的冰锥,直刺张伟强的心脏,“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了算。”每一个字都像冰雹砸在冻土上,断绝了他所有的幻想。
“第二,”她的声音陡然更冷了几分,带着彻底的切割和驱逐意味,“以后,别叫我‘老婆’。”她微微俯身,拉近了距离,让张伟强能更清晰地看到她眼中那深不见底的鄙夷和厌恶,红唇轻启,吐出淬毒的冰凌:“你,不配。”
“最后,”她直起身,姿态如同女王俯瞰尘埃,用下巴极其轻蔑地点了点一片狼藉的衣柜和他本人,“收拾收拾你这些…垃圾。”目光如同扫帚,扫过他身上的污秽和衣柜里那些沾满他干涸精液的衣物、柜壁,“赶紧滚。”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不容抗拒的驱逐令,“这几天别让我在这个家里,再看到你。”
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铁锤,将他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和作为“家”的归属感彻底砸得粉碎。
说完,顾晚秋不再看他一眼,仿佛多停留一秒都是对自己感官的亵渎。
她利落地转身,赤裸的、布满欢爱印记和精液残留的成熟胴体,在晨光中划出一道冰冷而诱人的弧线。
她迈着稳定而带着一丝纵欲后慵懒疲惫的步伐,臀瓣随着走动微微颤动,留下若有若无的精液气息,径直向主卧卫生间那扇紧闭的、正传来哗哗水声的门走去。
张伟强如同被抽掉了所有骨头和灵魂,彻底瘫软在衣柜冰冷肮脏的角落里。
顾晚秋那冰冷如刀的话语,尤其是最后那轻蔑到极致的“不配”和“垃圾”,将他最后一点残存的、如同蛛丝般脆弱的希望和尊严彻底碾碎,挫骨扬灰。
他张着嘴,喉咙里像是塞满了滚烫的沙砾,只能发出无声的、剧烈的哽咽,滚烫的泪水混合着脸上的污垢和冷汗,汹涌而下,在肮脏的衬衫前襟洇开深色的湿痕。
巨大的悲恸和一种荒谬到极致的讽刺感让他浑身冰冷麻木,仿佛血液都已冻结。
他像一具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提线木偶,机械地、无比艰难地从狭窄污秽的衣柜里爬出来。
双腿因长时间蜷缩而麻木刺痛,如同有千万根针在扎,几乎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
他佝偻着背,像一只被彻底打垮的老狗,不敢看那张凌乱的大床上残留的欢爱痕迹,不敢看墙壁上那幅被儿子精液玷污的婚纱照,只想尽快逃离这个将他尊严彻底撕碎的地狱。
就在他踉跄着,胡乱抓起几件散落在地上、同样沾染了灰尘和他自己干涸精液污迹的衣物,塞进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时——
主卧卫生间紧闭的门内,持续的水声似乎变小了。
紧接着,隔着那扇并不十分隔音的门板,清晰地、毫无阻碍地传了出来:
顾晚秋那熟悉的、此刻却带着极致媚惑、放纵和毫不掩饰享受的呻吟,如同烧红的铁钩,狠狠勾住了张伟强的神经:“嗯啊~辰辰老公…别…别舔那里…啊哈~!痒…痒死了…”
声音甜腻得能滴出蜜糖,带着撒娇般的颤抖。
随即是张辰低沉、满足、带着浓浓占有欲的喘息和调笑,清晰地穿透门板:“妈…下面这张小嘴…比上面还馋…流这么多水…昨晚没喂饱你?”
伴随着一阵更加粘腻的、仿佛口舌交缠的“啧啧”水声。
紧接着,顾晚秋的呻吟陡然拔高,带着被顶撞到深处的哭腔:“呀啊——!进…进来了!好深…辰辰…用力…再深一点…啊哈~!好爽…顶…顶到花心了…呃呃呃…用力肏妈妈…肏烂妈妈的骚屄…”
这淫声浪语,如同最猛烈的毒药,又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张伟强早已破碎不堪、鲜血淋漓的心脏上!
他身体猛地一僵,如同被高压电流击中,脸上瞬间失去最后一丝血色,只剩下死灰般的、彻底的绝望。
这声音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宣告他彻底出局、被亲生儿子从身体到心灵完全取代的终场哨音。
他最后一点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幻影,在这毫不掩饰的欢爱之声中被彻底撕碎、践踏成泥。
“呃…!”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如同濒死野兽般的、短促而破碎的呜咽。
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手脚并用地冲出了主卧,冲过了弥漫着隔夜情欲气息的客厅,冲向那扇象征着“家”的大门。
他不敢回头,不敢停留哪怕一秒,仿佛身后有择人而噬的恶鬼。
“咔哒。”
身后,张家那扇厚重的、曾经无数次被他开启关闭的大门,被他从外面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带上。
落锁的机械声清脆、冰冷、决绝,如同最终的审判槌音,沉重地敲下,将他与门内那个曾经属于他的世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曾经拥有的一切——彻底、永久地隔绝开来。
清晨微冷的空气中,张伟强佝偻着背,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手里拎着那个寒酸得可怜的、装着几件脏污衣物的塑料袋,失魂落魄地站在公寓楼冰冷空旷的楼道里。
他身上散发着汗臭、灰尘和精液干涸后的浓重腥膻味,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脸上泪痕混合着污垢,狼狈不堪。
身后,是那扇紧闭的、将他彻底放逐的家门。门内,那让他心胆俱裂、象征着彻底取代的欢爱之声,透过门缝,依旧隐约可闻,如同魔音灌耳。
他茫然地转动着空洞的眼珠,看向冰冷的、反射着惨白晨光的金属电梯门,看向通往楼下、仿佛没有尽头的幽暗楼梯间。
世界之大,晨光熹微,邻居的门内隐约传来早餐的香气和孩童的笑语。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被冰冷的铅块堵死,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冰冷的泪水再次无声地、汹涌地滑过肮脏的脸颊,砸落在冰冷坚硬的地砖上,碎裂成更小的、无人问津的水渍。
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天地苍茫,竟再无他立锥之地。
明明是炎热的夏天,张伟强却只感觉到刺骨的冰冷,他拿着随便选了个方向离开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