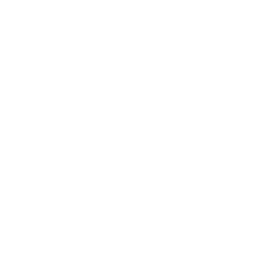被囚禁的日子,梁焉非完全不知道时间是如何流逝的,只知道换药的人来了七次,秦受也来过,而他口中,要给他讲故事的谭贺殊始终没有出现。
这里的技术的确够高端,新伤旧伤一起,他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手脚上的铁环依旧没有去除,像个犯人一样被拘在一张床榻上。
例行公事一样,又有人来替他检查身体,习惯是很可怕的东西,在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之前,他就主动翻过了手腕,他们往常都会抽一管他的血带走。
梁焉非压下心底的郁结,又把手腕转了回去,他的敏锐度被日复一日的禁锢磨损了,动作变得迟滞且呆板,眼睛沿着左臂的方向看去,看清站在一旁的人时,明显一愣。
两人对视着,明明距离不过尔尔,却像隔了山海之远,一生之遥。
梁焉非还不知道,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谭贺殊神情如常,在床沿坐下,看着他说:“恢复得不错。 ”
“秦受说,你想见我?”
梁焉非想了想,他好像没这么说过,不知道秦受怎么跟他说的,不过他确实有很多想问的。
“禁区的塌陷,和你有关?”
谭贺殊不再避讳,他说:“是。 ”
“… 为什么这么做? ”
“为了毁掉生一计划。”
梁焉非沉默了,他一直知道生一计划中有不稳定因素存在,原来核心本身就有问题。
他说毁掉生一计划,梁焉非不知道是怎样的毁掉,但如果他成功了,培春霞现在一定不会好过,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这就是你想要的?也包括毁了培春霞吗?”
谭贺殊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瞬间警觉起来,果然,无论过去多久,从谁的口中听见,他都无法坦然面对这三个字。
谭贺殊没有理会,只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梁焉非,你可别没大没小,知道吗,你应该叫她姐姐。”
梁焉非没有问过她生日,自然不知道她比自己大还是小,但是谭贺殊突然说起,他不觉得谭贺殊是在指年龄。
“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为什么,你能在那次边境调查中活下来,谭琮,也就是我的父亲,和你做了基因比对,确定了你是他的孩子,知道梁却不仅把你生下来,还把你养大了,他一高兴,发了慈悲心就把你放了,反正你一个人也调查不出什么,放过你也没关系。”
梁焉非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他。
“不理解?呵,我也没理解过,可这就是事实,说起来你在梁却肚子里的时候我们还见过,如果不是我那天打开地下室的门,梁却根本没机会跑,可他是怎么报答我的?哈哈,真够有良心的。”
“你…就算你说的是真的,跟培春霞又有什么关系?”
这事太扯了,仅凭谭贺殊一面之词他没办法相信,即便他内心深处都开始认同,难怪这么多年来梁却对他这个独子如此冷漠,难怪他从来不知道有关母亲的一丁点信息。
谭贺殊不回答,动手扯开衬衣最上面的扣子,皮肤上布满暧昧的红痕,梁焉非也曾无数次在那之上留下痕迹,所以很清楚他做了什么。
谭贺殊对这种事有瘾,他控制不了,作为炮友,曾经的梁焉非很乐意跟他睡觉,毕竟他又骚又耐操,很适合被肆意作践,发泄性欲。
但现在不一样了,谭贺殊是敌人,除了仇恨,他不会产生这之外的任何情感。
他略带厌恶地撇开头,谭贺殊走上前,捏着下巴把他头扳回来,反手扇了他一耳光。
他用了很大力气,梁焉非的嘴角当时就破了,他用舌头抵了抵,血腥味在舌尖蔓延开。
“你打我的次数还少吗,还你一下而已。”谭贺殊一边揉手,一边“好心”解释。
谭贺殊继续解衬衣的扣子,大片大片的青紫皮肤暴露出来,又可怜又凄惨,像是受了多严重的伤似的。
谭贺殊把手滑向下方,开始隔着裤子挑逗他的下体,眼里的疯劲收不住。
“多亏谭琮,我们有一半相同血缘,这么做,算乱伦吗?”谭贺殊喃喃自语,显然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梁焉非挣脱不开铁环的桎梏,在无比熟悉的挑逗手法之下,他发现自己可耻地硬了。
“哈,梁焉非,”谭贺殊也发现了,他一把扯下梁焉非的裤子,抓住高高翘起的物什,抬眸嘲弄地看向梁焉非,“你的这玩意可比你这个人好得多。”
谭贺殊把裤子踢蹬走,跨到梁焉非身上,掰开屁股,湿润微张的穴口对准鸡巴随时准备坐下去。
梁焉非气得头昏,咬牙问他:“谭贺殊,你有这么欠吗?”
谭贺殊坐落的动作一顿,只用股缝上下磨了磨,流出的水黏腻拉丝。
“不喜欢?”谭贺殊眯起眼睛,感受到那东西很诚实地顶到他屁眼上,毫不掩饰插他的欲望。
谭贺殊不在意他说的,反正更过分的他都被骂过无数次了。
他使劲往两边撑开穴眼,先将硕大的龟头吞吃进去,然后便一坐到底,久违的结合让互相怨恨的两个人心里升腾起诡异的满足。
即便再多隔阂,他们的身体还是依旧无比熟悉对方。
不同的是,往往被干地死去活来的谭贺殊今日成了主导者,他抬起屁股努力起落,用暖热的肠道包裹住那根同样炙热的鸡巴,自主寻找着体内可以让他高潮喷水的骚点。
他们周身的空气变得潮湿且火热,灼烧着他们交合碰撞的身体,可那两双眼睛还是始终如一的冰冷,谭贺殊倒是很少在做的时候露出这么冷静的表情,尤其还是在他主动求欢的情况下。
“…啊……操我那里…快…”谭贺殊察觉到他的抗拒和躲避,居高临下撑在梁焉非身上,抬手又是一巴掌,冷声呵道:“操我。”
梁焉非一身反骨这时候是一点用都没有,插都插了他还能假装两人是在仰卧起坐吗。
他压沉声线,语气不善:“我这样要怎么操你,你自己往下坐点。”
谭贺殊欣赏他脸上的屈辱,愤怒,难堪,还有自己扇出来的巴掌印,心情一好,下面的确是坐得更深了。
“梁焉非,你把我…嗯…当狗玩的时候,想得到有…啊哈……今天吗?”
“我其实…没那么恨你的,各取所需罢了,可是……”
话说到这,谭贺殊伸手扯了一把乳头的银环,穿刺的孔洞中因此渗出了血丝。
做到兴头上,或者极端焦躁的情况下谭贺殊就会像这样惯性自虐,被玩出来的,改都改不掉。
“你…为什么要跟我…嗯…抢倍倍,因为梁却,我已经…失去过她一次了……”
“梁焉非…你知道她是你姐姐吗…”
谭贺殊只顾自己爽,丝毫不管梁焉非的感受,他大病初愈,精力本就不够,被谭贺殊索取到头晕发胀,冷不丁听见他说什么姐姐,这话过了一下脑子,一时也没反应过来到底什么意思。
“什,什么?”
“她当年出生…啊哈…就被梁却丢了,是你的亲姐姐,”
“你让她碰你了?比起…唔…跟我做,更算乱伦……”
“你闭嘴!不可能!”
梁焉非疯了一样挣动,把铁床摇晃地叮当响,连带着骑在他身上的谭贺殊也被耸得不成样子,谭贺殊没有精力再去打他一巴掌,也不打算把鸡巴拔出来,他只是迎合着这样狂乱节奏继续摇屁股,昂头乱叫,直到梁焉非违背不了生理意志,射进他里面为止。
两个人各疯各的。
谭贺殊翻身下床的时候两腿打颤,白浊顺着大腿直往下淌,他扯过床单擦干,提裤子的时候看了眼梁焉非,满脸生无可恋,手腕处一道道血瘀,看起来比他这个被干的还惨。
他自认自己还算可以了,等梁焉非以后接触实验,变成傻子都有可能,至少在他有意识的时候,他告诉了他真相,至于他能不能接受,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他谭贺殊不能接受的事也多,最后还不是都接受了。
这一炮,就算他讨的债吧,至于他们之间到底欠了些什么,谭贺殊也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