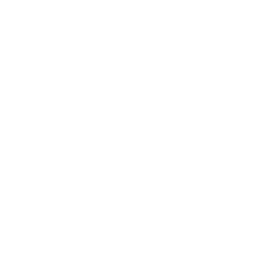一
风像是砂纸,贴着314国道粗粝地打磨着天地。远处天山雪顶在热浪里浮动,像海市蜃楼。我背着塞得鼓鼓囊囊的登山包,竖起拇指,站在库尔勒通往喀什方向的荒野岔口。瑜伽裤紧裹着双腿,吸饱吸了日头的毒辣,布料下的皮肤烫得发痒。汗水沿着脊椎沟往下淌,洇湿了运动背心后腰那一小圈深紫色的布料——那是我最爱的颜色,此刻黏腻地贴在身上,像一道羞耻的烙印。
一辆红色、沾满泥浆的重型卡车,吭哧吭哧喘着粗气,在我面前刹住。车轮卷起的粗粝沙尘扑了我满头满脸,迷得眼睛生疼。副驾驶的车窗摇下,露出一张被戈壁阳光反复鞣制的深棕面庞。他鼻梁高挺,眼窝很深,浓密的黑色卷发从一顶磨旧了的鸭舌帽下桀骜不驯地钻出来。烟味和一种混合着汗味、机油、还有浓烈孜然香料的气息,瞬间冲进我的鼻腔。
“去哪?”他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维语口音,舌尖卷动,沙哑得像被砂石磨过。
“喀什方向,能搭一段吗?”我努力挤出被风吹得干涩的笑容,手指下意识攥紧了背包带子。
他叼着半截烟,上下扫了我一眼,目光刀子般刮过我紧绷在瑜伽裤里的臀线,最后落在我汗湿的胸口。那视线没什么温度,只有一种近乎评估货品的审视。烟灰被他弹在滚烫的地上。“上来吧,后面。”他朝后座歪了下头,不再看我,仿佛只是随手捡了块路边的石头。
驾驶室像一个蒸笼,闷热、拥挤,充斥着更浓烈的男人体味和柴油气息。巨大的方向盘几乎占据了他半个身体的空间。车发动起来,引擎沉闷地轰鸣,震得座椅都在抖。窗外,戈壁的苍黄与天空的刺眼蓝白在远处交汇,单调得令人窒息。路况极差,车身颠簸得像一匹不肯驯服的野马。每一次剧烈的弹跳,我的身体都会不受控制地撞向他粗壮的手臂,或者被离心力甩向坚硬的车门。隔着薄薄的瑜伽裤,每一次摩擦都清晰地传导着陌生男性躯体的热度、肌肉的力量感。
“名字?”他盯着前方仿佛没有尽头的搓板路,打破沉默。
“张新雨。”我小声回答。
“艾力。”他简短地回了一句。接着又是漫长的沉默,只有引擎的嘶吼和车体金属部件在颠簸中痛苦的呻吟。他偶尔会哼一两句调子奇异的维语歌谣,短促,低沉,像沙漠里的风掠过枯骨。
车子驶入一片更为荒凉的腹地,地貌变成了嶙峋的黑色怪石和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远方只有地平线和偶尔掠过的、惊慌失措的沙鼠影子。就在这时,艾力猛地一打方向盘,卡车咆哮着冲下路基,在一片相对平坦的洼地停了下来,卷起的尘土像黄色的幕布,瞬间遮蔽了车窗外的世界。
引擎熄灭。世界骤然安静得可怕,只剩下车轮下碎石被高温烘烤发出的轻微噼啪声,以及……我们两人粗重不一的呼吸。艾力啪嗒一声按开了顶灯,昏黄的光线笼下来,把他棱角分明的侧脸投在车窗上,也照着我无处遁形的紧张。
他没回头,兀自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叼上一支点燃。烟雾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带着一种辛辣的、宣判般的意味。
“女人,”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得像压在戈壁上的乌云,每一个字都敲打着我的耳膜,“知道戈壁滩的规矩吗?”他缓缓转过头,那双深陷的眼睛像两口幽深的古井,直勾勾地盯着我,里面没有询问,只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猛兽盯上猎物的笃定。那目光沉沉地落在我身上,尤其在我被汗水浸透、紧紧包裹的胸口和臀部线条上反复刮擦。
我的心猛地沉下去,撞得肋骨生疼,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全身的血液似乎在瞬间涌向头顶,又在下一秒冰凉地褪去。手指死死抠着粗糙的座椅边缘,指甲几乎要嵌进那布满裂纹的塑料里。“什…什么规矩?”我的声音干涩得发颤,尾音飘忽得如同风中的游丝。
他没回答。只是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突然伸出手,带着烟味和浓重孜然味的手指,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猛地掐住了我的脖子!并不十分用力,却足以让我瞬间僵直,像被钉在砧板上的鱼。
“少他妈在这里装!”他低吼,喷出的烟雾呛得我眼泪瞬间涌出,视线一片模糊。那声音里的轻蔑和暴戾,像鞭子抽打在我的神经上。“穿成这副骚样,跑到这种鬼地方来搭车?”他粗糙的手指恶意地划过我颈侧跳动的脉搏,又往下,隔着薄薄的、汗湿的瑜伽背心布料,重重地捻过我的乳尖。一阵尖锐的、混合着羞耻和异样电流的刺痛猛地窜过脊椎。
“你们这些城里的‘乖’女孩,”他发出一声短促、刺耳的冷笑,每一个字都淬着剧毒的冰,“骨子里不就是人人上的‘公交车’?嗯?”
那两个字——“公交车”——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耳膜上。瞬间,一股滚烫的、完全不受控制的暖流,猛地从身体最深处炸开,疯狂地向下腹涌去!我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隐秘的布料迅速地被一股湿热的液体浸透,紧紧地黏在了皮肤上,勾勒出羞耻的形状。脸颊烧得滚烫,像被人狠狠抽了无数个耳光。我张了张嘴,想反驳,想尖叫,想骂他疯子。可喉咙里堵得死死的,只剩下破碎的气音。巨大的耻辱感像山一样压下来,可耻的是,身体深处那隐秘的、被粗暴话语点燃的痉挛般的悸动,却更加疯狂地冲刷着我的理智。
“说话!”他猛地收紧手指,虎口卡着我的喉骨,窒息感瞬间攫住了我。
“不…不是…”我徒劳地挣扎,窒息带来的生理性泪水不断滚落,狼狈地划过滚烫的脸颊。混乱中,手肘猛地撞到了冰冷坚硬的方向盘,发出哐当一声闷响。
这声响似乎更加激怒了他。艾力眼中戾气暴涨,像是被彻底点燃的野火。“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低咒一声,掐着我脖子的手骤然松开,在我本能地弓起身子大口喘息的瞬间艾力松开我脖子的瞬间,冰冷的空气像刀片一样刮过喉咙。我剧烈呛咳起来,肺叶火烧火燎,眼泪鼻涕糊了满脸。可还没等吸进第二口完整的气,头皮就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他粗硬的手指狠狠插进我汗湿的发根,像抓牲口似的猛地将我整个人往下按。
“呜——!”我被迫矮下身子,额头“咚”一声撞在硬邦邦的驾驶台边缘,震得眼前金星乱冒。浓烈的机油味、他裤裆里蒸腾出的雄性汗味、还有那该死的孜然气息,混成一股令人窒息的浊流,死死堵住我的口鼻。
“装什么死狗!”他粗声低吼,膝盖蛮横地顶开我试图蜷缩保护自己的腿。那只带着厚茧、沾着黑乎乎油污的大手,毫无预兆地、粗暴地探进我被汗水浸透的瑜伽裤腰侧!廉价弹力布料发出不堪重负的“刺啦”一声,从腰际到大腿外侧瞬间豁开一道长长的裂口。
冰冷的空气猛地舔上暴露的皮肤,激起一片鸡皮疙瘩。下一秒,他滚烫粗糙的手掌像烙铁一样直接摁了上来,沿着我赤裸的臀缝狠狠揉捏下去,力道大得几乎要把骨头捏碎。皮革座椅破开的口子像无数细小的牙齿,啃噬着被迫压在它上面的臀肉,摩擦的刺痛火辣辣地蔓延。
“啊——!不要!放开!”我终于从窒息的眩晕和剧痛中找回一丝声音,带着哭腔,徒劳地扭动身体。可那点挣扎在他铁箍般的手臂压制下,脆弱得像被蛛网缠住的飞虫。指甲划过他肌肉虬结的小臂,只留下几道微不可见的白痕。他另一只手已经探到前面,扯着破碎的裤腰,连同底下那层薄得可怜的底裤,一起猛地撕了下来!
布料彻底离开身体的瞬间,一种灭顶的羞耻感几乎将我击垮。赤裸的下半身毫无遮蔽,暴露在昏黄顶灯下,暴露在戈壁滩死寂的空气中,暴露在他那双鹰隼般攫取的眼睛里。臀下冰凉的塑料裂纹像蛇一样蜿蜒,硌着柔软的皮肉,带来尖锐冰冷的触感。我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一丝腥甜的血味,身体抖得像深秋枝头最后一片叶子。
“看见没?”艾力嗤笑一声,带着浓重的鼻音,粗糙的手指毫无怜惜地戳进那已经泥泞不堪、温热黏滑的入口,恶意地搅动了一下。“水多得都他妈能养鱼了!还跟老子装?”那下搅动像通了电,一股无法抗拒的酸麻猛地从脊椎炸开,直冲天灵盖。喉咙里不受控制地泄出一声尖锐的、甜腻的抽泣,身体深处像有根弦被狠狠拨动,激荡出羞耻又汹涌的浪潮。
我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大脑一片空白。身体背叛意志的强烈反应比刚才的撕扯更让我崩溃。他怎么知道?他怎么敢……
“公交车站牌都不用立,自己就流水等客了?”他恶毒的嘲讽像淬了毒的针,精准地扎进我最卑微的神经末梢。那只带着油污和烟味的手掌猛地扬起,裹挟着风声,“啪!”一声脆响,结结实实扇在我完全暴露的臀肉上!
剧痛!火辣辣的剧痛伴随着巨大的羞辱感炸开。雪白的皮肉上瞬间浮起一个清晰的、泛着油光的通红掌印。臀峰被打得猛烈晃动,细小的肉浪在昏黄灯光下颤巍巍地跳荡。那清晰的痛感像一道电流,非但没有熄灭身体里那簇可耻的火苗,反而像泼了油,激得它“轰”一下窜得更高!小腹深处拧绞般地收缩,一股更加汹涌的暖流失控地涌出,黏腻地沿着大腿内侧滑下,在冰冷的塑料座椅上留下一道湿亮的水痕。
“呜……别打……”我带着浓重的哭腔哀求,声音破碎不堪,身体却在他手掌的压制和那羞耻的生理反应下,不受控制地塌下腰肢,将饱受蹂躏的臀部拱得更高,像是无声地、卑贱地迎合。汗水、泪水混在一起,顺着下巴滴落在布满灰尘的驾驶台面板上,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小点。身下的塑料座椅,那冰冷粗糙的裂纹,此刻像无数张贪婪的嘴,吮吸着、摩擦着我被迫献祭出的羞耻和滚烫的潮湿。
艾力那只带着油污和烟味的手掌,在响亮地拍打过我的臀肉后,并没有离开。反而像盘踞在猎物上的猛兽,五根粗粝的手指深深陷入那被扇得通红、火辣辣疼痛的软肉里,用力地抓握、揉捏。粗糙的茧子刮擦着敏感的皮肤,每一次挤压都激起一阵尖锐的刺痛,混着一种让我浑身发毛、却又无法抗拒的酸麻,电流般窜上尾椎骨。
“疼……”我呜咽着,身体在他强硬的钳制下绷得像张拉满的弓,被迫弓起的腰肢让臀峰更加突出地暴露在他的掌控下。汗水顺着脊柱沟蜿蜒流淌,滴落在冰冷的塑料座椅上,和那些羞耻的湿痕混在一起。
他没理会我的痛呼,另一只手粗暴地抓住我汗湿的头发,毫不留情地将我的脸向后扳去。后颈传来可怕的拉伸感,几乎能听到筋骨的呻吟。视野被迫上仰,直接撞进他俯视下来的、幽深的眸子里。那里面没有情欲,只有冰冷的审视和一种……纯粹的、近乎原始的支配欲。
“看着!”他命令道,声音硬得像戈壁滩的石头。那只揉捏着我臀部的手猛地向两边掰开,指尖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强行挤开臀缝深处最私密、最脆弱的褶皱!暴露在浑浊空气里的隐秘入口猛地瑟缩了一下,能清晰地感觉到晚风带着沙砾的气息拂过那最敏感、最羞耻的所在。
“啊——!”我失声尖叫起来,巨大的羞辱感像冰水灌顶,瞬间冻结了血液。身体像是被剥光了最后一丝遮羞布,赤裸裸地、毫无尊严地被钉在祭台上。
“看清楚你自己!”艾力低沉的嗓音像砂轮磨过耳膜,带着一种审判般的残酷,“这地方,天生就是挨操的!装什么清高?”他粗糙的指尖恶意地在那敏感的入口边缘刮了一圈,激起一阵剧烈的痉挛和更汹涌的湿热涌出。
话音未落,他松开了掰开臀缝的手,却并非放过。只听到金属皮带扣“哗啦”一声脆响,紧接着是拉链被猛地拽下的刺耳声音!皮革摩擦衣料的窸窣声后,一股滚烫的、蓄势待发的雄性气息扑面而来,混合着汗味和更浓烈的皮脂气味,瞬间充斥了我被迫仰起的鼻腔。
他甚至没有完全褪下裤子。那根怒张的、烙铁般的凶器就那样带着蛮横的力量,毫无缓冲地顶了上来!前端硕大的头部带着惊人的热度,粗暴地抵住那被强行暴露、正因恐惧和可耻的生理反应而微微翕张的入口,像攻城槌抵住了城门。
“唔——!!”巨大的异物感和即将被撕裂的恐惧让我瞬间绷紧了全身的肌肉,所有的声音都被掐死在喉咙里,只剩下破碎的、嘶嘶的抽气。指甲深深地抠进破旧座椅的塑料里,试图抓住点什么,却只抓到了一手细微的碎屑。
艾力没有给我任何适应的时间。他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死死扣住我赤裸的髋骨,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几乎要捏碎骨头。另一只手依旧牢牢抓着我的头发,迫使我的脸对着前方布满灰尘的车窗。窗外是死寂的戈壁,茫茫黄沙映照着我惊恐失神、泪水横流的倒影。
然后,他腰部猛地向前一送!
“呃啊——!!!”一声凄厉到变调的惨叫终于冲破了喉咙,像濒死野兽的哀嚎。剧痛!一种从未想象过的、被活生生劈开的剧痛从身体最深处爆炸开来!那滚烫粗硬的凶器像烧红的铁钎,毫无怜悯地、强横地撑开紧致脆弱的甬道,撕裂着每一寸从未被如此粗暴对待的柔软黏膜,朝着更深、更灼热的区域狠狠撞进去!
没有温柔,没有试探,只有蛮横的贯穿和占有。皮革座椅吱嘎作响,随着他每一次凶狠的顶撞而剧烈晃动,配合着车身外呼啸的风沙,演奏着一曲荒诞而暴虐的交响。每一次冲击都像要把我的内脏从喉咙里顶出来,身体被撞得在狭窄的驾驶座上前后晃动,赤裸的臀肉一次次重重地拍打在他覆盖着粗糙布料的结实小腹上,发出沉闷的“啪啪”声。
疼痛像海啸般吞噬着意识,眼前阵阵发黑。汗水、泪水、还有喉咙深处因为剧痛泛上的腥甜味道混在一起。我像断了线的木偶,只能随着他狂暴的节奏无助地摇晃,每一次深入都伴随着骨骼和内脏被挤压的闷痛,每一次抽出都带出黏腻的水声和撕裂的钝痛。牙齿死死咬住下唇,铁锈味在口腔里弥漫,却丝毫无法缓解那被贯穿、被填塞、被彻底碾碎尊严的绝望。
“呜…哈啊……”破碎的呻吟和抽泣完全不受控制地从喉咙深处泄出,断断续续,夹杂着剧痛带来的倒气声。身体在极度的疼痛和那无法言说的、被暴力激活的羞耻本能间撕裂。每一次他凶狠地撞到最深处,撞击着某个隐秘的开关,那足以淹没理智的尖锐酸麻感就会短暂地压过疼痛,带来一阵失控的、湿热的痉挛,紧接着又被他下一次更猛烈的冲撞碾得粉碎。
艾力沉重的喘息喷在我的后颈,带着胜利者的粗野。他抓住我头发的手猛地向后一拽,迫使我痛苦地仰起头,脖颈的线条绷紧得像要折断。他那带着浓重孜然味和烟味的唇舌,像野兽啃噬猎物般,粗暴地啃咬上我被迫暴露的脆弱喉管,留下湿漉漉的、带着刺痛感的印记。
“叫!”他含糊不清地命令着,牙齿不轻不重地碾磨着那块敏感的皮肉,下身却依旧保持着狂暴的节奏,每一次顶入都像要把我钉死在方向盘上。“让你叫就给老子叫!公交车的喇叭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