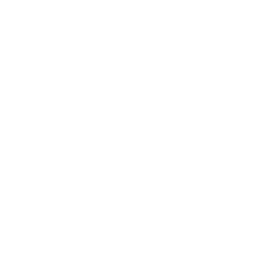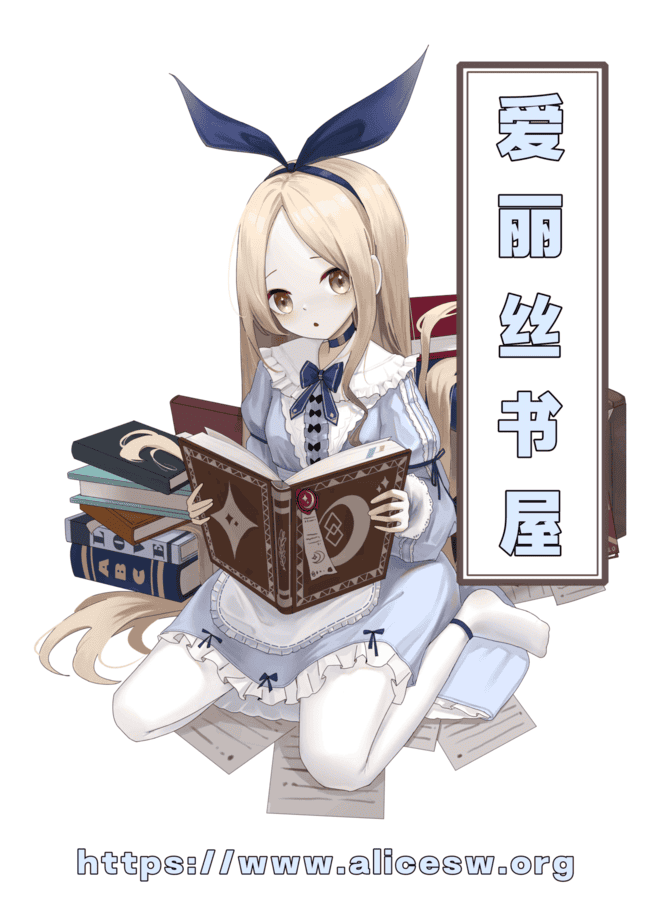五
那毁灭性的痉挛终于像退潮般缓缓平息下来,留下身体深处一片狼藉的、被彻底掏空又塞满的麻痹,以及更加强烈清晰的撕裂灼痛。每一次微弱的呼吸都牵扯着下身的伤口,火烧火燎。老马浑浊的喘息声如同破风箱,带着巨大的满足和一丝疲惫,重重地压在我身上。他滚烫人的汗液和浓烈的体味混合着猪食的馊臭,黏腻地糊在皮肤上。
他粗糙油腻的手,带着一种施舍般却又充满掌控欲的力道,重重拍了拍我沾满泥污和汗水的脸颊,发出啪啪的轻响。
“妈的……真够劲……”他意犹未尽地嘟囔着,浑浊的眼睛里还残留着兴奋的余烬,“大城市来的‘小母狗’……果然跟村里那些娘们不一样……够骚!” 他嘿嘿笑起来,那笑声在空旷冰冷的仓库里回荡,带着令人作呕的回音。
他沉重地挪开身体,满足地提起他那同样肮脏的工装裤,皮带扣发出刺耳的金属刮擦声。那根刚刚施暴的器物软垂下来,上面沾满了暗红的血丝、浑浊的粘液和他自己污浊的体液,散发着一股浓烈到令人窒息的腥臊。
我瘫软在冰冷肮脏的地面上,像一具被彻底撕碎又胡乱拼凑起来的破布偶。下身撕裂的剧痛一阵阵传来,如同永不熄灭的阴火。腿间一片粘腻狼藉,混合着血液、泥水、精液和其他污秽,冰冷地糊在皮肤上。胃里那团冰冷馊臭的糊状物,在刚才剧烈的痉挛和承受中翻搅得更厉害,灼烧着食道。屈辱感如同滚烫的沥青,从头到脚浇灌下来,凝固了每一寸皮肤。最深的羞耻,却来自身体深处那阵刚刚过去、无法自控的剧烈痉挛——那是对意志最彻底的背叛!
老马提好裤子,又踢了踢地上那个破瓦盆,发出咣当的声响。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浑浊的眼睛扫过我残破不堪、沾满秽物的身体,尤其是下身那片狼藉。
“啧,弄成这样……”他嫌弃地皱了皱鼻子,随即又不怀好意地咧嘴笑了。他转身走到角落里那个积满灰尘和污垢的大水缸边,再次抄起那个边缘破损的破搪瓷瓢,哗啦一声,舀起满满一瓢浑浊发黄、漂浮着杂质的水。
他端着水走回来,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如同冲洗牲口般的随意,手臂一挥!
“哗——!”
冰冷刺骨、带着浓重土腥和铁锈味的脏水,再次如同鞭子般抽打下来!水流粗暴地冲刷着胸腹间的淤青掐痕、锁骨上的伤口、脸上糊成一团的泥污泪痕,最后,毫不留情地冲向那饱受蹂躏、如同被捣烂的伤口般的下身!
“呃啊——!”冰冷的水流猛地冲刷在肿胀破皮的入口和撕裂的伤口上,如同无数根冰针狠狠扎进新暴露的神经末梢!剧烈的刺痛让身体猛地弓起,又被强行压下!
水流不仅带来了剧痛,更带来了彻骨的冰冷。本就因失温而不断颤抖的身体,更像是掉进了冰窟窿,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浑浊的脏水裹挟着血丝、精液的浊白和各种污秽的粘稠,在地面上汇聚成一小滩,散发着更加复杂的、令人作呕的腥臭。
老马看着地上那滩混杂的污水,又看了看我蜷缩颤抖、簌簌发抖的样子,似乎觉得已经完成了“清洁工作”。他满意地扔掉破瓢,目光扫过仓库,最后落在那堆散发着霉味的稻草垛上。
他走过去,从那巨大的草垛上,粗暴地扯下几大把干枯、散发着浓烈霉味的稻草,胡乱地扔在我旁边的泥地上。
“喏!”他踢了踢那堆稻草,像是给牲口扔了把干草,“自己铺铺!冻死在这,老子可亏了两千块!”
说完,他不再多看我一眼,转身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仓库大门。沉重的木门被用力拉开,他矮壮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浓重的黑暗里。接着,是铁链缠绕的哗啦声,以及那把巨大铁锁落下的、冰冷决绝的“咔哒”声。
仓库重新陷入了死寂和彻底的黑暗,只有高处气窗透进一点模糊的星光。冰冷刺骨的湿寒如同无数条冰冷的毒蛇,从湿透的皮肤不断钻入骨髓。身体在剧烈的颤抖中,每一处伤口都在尖叫。身下的泥地冰冷僵硬,散发着土腥和污水的味道。旁边那堆散发着浓烈霉味的稻草,像一堆腐烂的枯骨。
身体深处,除了那清晰的、如同被火燎过的撕裂疼痛,似乎还残留着刚才那场毁灭性痉挛带来的、麻痹般的空洞感……以及一种更深的、如同深渊般的冰冷绝望。
冰冷,像无数根钢针扎进骨头缝里。
我是在一阵无法抑制的、剧烈的寒颤中醒来的。意识像是沉在浑浊冰冷的深潭底部,被刺骨的寒意和无处不在的疼痛强行拽了上来。身体僵硬得像一块被随意丢弃在冰窖里的冻肉,每一处关节都在呻吟。
高墙上那唯一的气窗,透进来一点灰蒙蒙、毫无热度的晨光。光线里飞舞的尘埃都显得死气沉沉。空气里弥漫着昨夜的绝望气息——浓重到化不开的霉味、稻草腐烂的气味、土腥气、铁锈气……还有,那挥之不去的、暧昧又刺鼻的腥臊味,那是精液、血液、汗水和各种污秽混合后,在冰冷的空气里发酵了一夜的味道。
身体是散架的。稍微动一下手指,尖锐的刺痛就从手腕脚踝被暴力抓握过的地方传来。更糟的是下身。那里像被塞进了一整块燃烧的炭,灼热、钝痛,每一次微小的牵扯——哪怕是呼吸带来的腹部起伏——都让那撕裂的伤口剧烈地抽搐着发出抗议。腿间粘腻冰冷的感觉依旧存在,干涸的血迹、精斑、还有昨夜那瓢脏水留下的污渍,混合着身体深处不受控制分泌出的、带着淡淡甜腥的粘液,牢牢地粘在皮肤上,像一层凝固的耻辱。
胃里空空如也,但那种被强行灌入馊臭糊状物的恶心感还在,灼烧着食道。喉咙干得像是被砂纸磨过,每一次吞咽都带来刮擦般的痛楚。膀胱深处传来一阵阵强烈的、几乎要失控的坠胀感,比昨夜更甚!
就在这时,仓库外传来一阵清晰的、不紧不慢的脚步声。不是老马那种沉重急切的咚咚声。这脚步声更轻,带着一种……刻意的从容?还有,一种拖沓的、像是破布摩擦地面的声音。
我像惊弓之鸟般猛地蜷缩起来,试图用那堆散发着浓重霉味的稻草遮盖住自己赤裸的下身和残破的衣衫。心脏在冰冷的胸腔里疯狂擂动,撞击着肋骨。
厚重的木门被推开一条缝,发出吱呀的呻吟。一个身影挤了进来。
不是老马。
门口站着一个老妇人。很老,背佝偻得厉害,穿着一件脏得看不出原色的、打满补丁的旧棉袄,深蓝色的裤腿沾满了泥点,裤脚磨得稀烂。她稀疏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绾着一个松垮的小髻,脸上沟壑纵横,像被风干的橘皮。那双浑浊发黄的眼睛,像两潭死水,毫无波澜地落在我的身上——赤裸的、布满青紫伤痕的腿,腿间那片狼藉粘腻的污秽,还有我惊恐失措的脸。
她手里拎着一个同样肮脏破旧的瓦罐,罐口冒着一点点微弱的热气。另一只手里,拖着一个边缘破损、看起来像是喂猫狗的土黄色旧搪瓷盆。
她只是看着我,没有任何表情。那目光没有厌恶,没有怜悯,甚至没有好奇。是一种彻底的、令人心底发寒的漠然,仿佛在打量一件被丢弃在角落、沾满污垢的破家具。
死寂在冰冷的空气中蔓延,只有她手中瓦罐里偶尔冒出的一点微弱的“噗噗”声。
终于,她动了。拖着那只破搪瓷盆,发出刺耳的刮擦声,一步一步,缓慢地走到我面前。浑浊的眼睛依旧盯着我下身那片狼藉。
然后,她干瘪的嘴唇动了动,发出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的声音,带着浓重得几乎化不开的老马沟土腔:
“尿。”
一个字。一个冰冷、简短的命令。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膀胱的坠胀感在她目光的注视下达到了顶峰,几乎要冲破束缚。可强烈的羞耻感像一张冰冷的铁网,死死罩住了我。在这样一个老妇人漠然的注视下,在这冰冷肮脏的地上,像牲口一样……
她似乎完全不在意我的反应,或者说,她根本没期待我有反应。她只是把那只边缘破损的旧搪瓷盆,“哐当”一声,扔在了我腿边的泥地上,距离那片污秽只有几寸远。
“尿盆里。”她又补充了一句,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是在陈述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实。那双浑浊的眼睛没有离开我的下身,仿佛在无声地催促:快点,别耽误工夫。
膀胱的痉挛一阵紧过一阵,生理的本能像汹涌的潮水冲击着理智的堤坝。那冰冷的搪瓷盆口,像一个屈辱的深渊。我死死咬着下唇,几乎尝到了血腥味,身体因为极度的羞耻和强制忍耐而剧烈地颤抖起来,带动着下身的伤口一阵阵撕裂般的剧痛。
老妇人就那么站着,像一尊佝偻的、没有生命的石像,耐心而冷漠地等待着。仓库里只有我无法抑制的、痛苦的颤抖声,和瓦罐里那微弱的、如同最后心跳般的“噗噗”声。
终于,在极致的胀痛和无法抗拒的生理压迫下,意志的堤防彻底崩溃了。
一股温热混浊的液体,带着浓烈的、无法掩饰的尿骚气,伴随着剧烈的痉挛和下身伤口被牵扯的尖锐刺痛,完全失控地、汹涌地冲出体外!哗啦啦地冲击在冰冷的搪瓷盆底,发出清晰而响亮的声响。
屈辱的泪水瞬间决堤,混合着脸上干涸的泥污流下。我猛地别过脸,不敢去看那飞溅的液体,不敢去看老妇人那死水般的眼睛,更不敢去看自己彻底失禁的身体。整个身体剧烈地抖动着,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灵魂深处涌出的、无边无际的羞耻和崩塌感。尿液冲刷在搪瓷盆上的声音,在死寂的仓库里被无限放大,如同对我最后一点尊严执行死刑的宣判。
尿液还在持续流出,带着一种释放后的虚脱和更深的绝望。老妇人看着那渐渐盈满盆底的浑浊液体,浑浊的眼珠似乎动了一下。她没再看我,弯下佝偻的腰,枯瘦如同鸡爪般、布满老人斑的手,端起了那只散发着浓重尿骚气的旧搪瓷盆。
她端着盆,转身,拖沓着脚步,走向仓库角落那个曾经放过水缸的地方。那里似乎有一个通往外面的小排水口?她动作缓慢而熟练地将盆倾斜,哗啦啦……代表着彻底屈辱的液体被倾倒出去的声音,在冰冷的墙壁间回荡。她甚至没忘记在那个积着污水的排水口边缘,用破盆的边缘磕了磕,抖掉最后的残液。
做完这一切,她放下空盆,又拎起那个一直冒着微弱热气的破瓦罐。她重新走到我面前,依旧带着那种令人窒息的漠然,将那瓦罐放在地上,靠近我蜷缩的身体。
罐口的热气里,散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混合着劣质油腥气、某种植物苦涩味的稀薄粥香,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如同饲料般的陈腐气味。
“吃。”又是一个冰冷的单字命令。
她没有给我任何容器,也没有勺子。瓦罐口很宽,边缘同样沾着污垢。意思再明白不过:像狗一样,直接用嘴去舔食。
瓦罐里那点微弱的热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几乎转瞬即逝。屈辱和绝望如同冰冷的铁枷,沉沉地压在身上。我看着那罐散发着怪味的稀粥,又看了看那个重新端起的、刚刚盛过我尿液的破搪瓷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强烈的呕吐感猛地涌上喉咙!
“呕——!”
喉咙深处爆发出无法抑制的干呕!酸苦的胆汁混着胃液猛地冲上口腔,灼烧着干裂的喉咙壁!但胃里空空如也,只有一股股痉挛的酸水涌出,滴滴答答落在冰冷肮脏的泥地上,留下几滩刺目的黄绿色污渍。
我蜷缩着,身体因为剧烈的呕吐反应而抽搐,每一次抽动都牵扯着下身撕裂的伤口,带来尖锐的刺痛,眼泪失控地涌出。
老妇人浑浊的、死水般的眼睛看着地上那几滩呕吐物,又看看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干瘪的嘴角似乎往下撇了一下。那是一种极淡的、甚至称不上表情的细微动作,却比任何厌恶都更冰冷刺骨。她没说话,只是把那个散发怪味的破瓦罐又往前推了寸许,粗糙的陶罐边缘几乎蹭到我赤裸的膝盖。那股混合着劣质油腥和植物苦涩的气味,混着呕吐物的酸臭,更加浓烈地钻进鼻腔。
她似乎在用沉默下达最后的通牒:吃,或者饿着。像牲口一样。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僵持中,仓库厚重的木门猛地被撞开!
“哐当!”一声巨响!
老马矮壮的身影裹着一股室外的冷风和更浓烈的牲畜气息闯了进来。他脸上的横肉松弛着,带着宿醉般的浮肿和尚未褪尽的狰狞餍足,浑浊的眼珠子扫过仓库。目光落在我身上——赤裸的下身,腿间那片狼藉,还有地上那几滩新鲜的呕吐物。
“妈的!一大早就给老子找晦气!”他粗嘎的嗓子带着浓重的痰音,像砂纸刮过铁皮。他几步冲过来,带着一股酒气混合着猪粪的恶臭,抬脚就朝那摊黄绿色的呕吐物狠狠啐了一口浓痰!
“呸!”黏糊糊的浓痰精准地落在那滩酸水上。
紧接着,他那双沾满泥浆和干涸污物的破胶鞋,毫不留情地、像碾死一只恶心的虫子一样,狠狠踩了上去!粗糙的鞋底带着湿泥和粪便的颗粒,在呕吐物和浓痰上用力地、反复地碾磨、拧转!发出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粘腻摩擦声!
“脏东西!给老子舔干净!”他一边碾着,一边低头朝我咆哮,唾沫星子混着口臭喷在我脸上,“老子花钱买来的牲口,就得知道规矩!该吃就得吃,该拉就得拉在盆里!敢吐?”他又重重一脚跺在那片被碾得稀烂的污物上,“就给老子舔回去!”
强烈的恶心感和屈辱如同海啸般冲击着我!那被反复践踏的呕吐物混合着浓痰和鞋底的污秽,散发出更加令人作呕的气息。胃部再次剧烈地抽搐起来,但这一次,除了酸水,什么也吐不出来了。身体的颤抖加剧,牙齿咯咯作响。
老妇人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像一尊真正的泥塑木雕。
“吃!”老马停止了践踏,那只肮脏的胶鞋就踩在那摊污秽旁边几寸的地方,散发着无声的威胁。他抬手一指地上的瓦罐,语气是不容置疑的凶狠,“现在!给老子吃干净!少一口,老子就把你脑袋按进那堆脏东西里!”
最后的抵抗在绝对的暴力和赤裸裸的饥饿面前土崩瓦解。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所有羞耻。我伸出颤抖得如同秋风落叶般的手,冰冷的手指触碰到同样冰冷的瓦罐边缘。那粗糙的陶质刮擦着指尖。
没有选择。
我低下头,像一条真正的、被驯服的狗,把脸凑近了瓦罐那宽大的、沾着污垢的开口。一股更加浓烈刺鼻的、带着发酵酸味的饲料气息扑面而来,混杂着铁锈和土腥。里面是浑浊的、粘稠度如同浆糊的液体,漂浮着一些煮烂的、无法辨认的深绿色野菜梗和可疑的黄色颗粒。
闭上眼,强忍着翻腾的胃液和喉咙口的灼烧感,嘴唇颤抖着贴上了那冰冷的罐口边缘。一股冰冷的、带着浓烈怪味的糊状物涌入口腔。它粘稠、粗糙,带着沙砾般的颗粒感,味道是难以形容的苦涩、酸涩和一种陈腐油脂的恶心混合体。牙齿碰到那些煮烂的菜梗,软烂得如同腐烂的纤维。
“呜……”喉头发出压抑的呜咽,身体因为抗拒而本能地后缩。
“吃!咽下去!”老马的咆哮就在耳边炸响,带着酒气的唾沫星子溅到脖子上。那只沾着呕吐污物的胶鞋威胁性地挪动了一下,几乎碰到了我的手。
恐惧像冰冷的钢针扎进脊椎!
我猛地将头更深地埋进瓦罐口,几乎是贪婪地、带着一种绝望的吸吮,让更多冰冷粘稠的糊状物涌入嘴里。粗糙的颗粒刮擦着口腔上颚和喉咙,那难以形容的怪味如同实质般塞满了所有感官。没有咀嚼——也根本无法咀嚼——只能靠喉咙的本能,艰难地、痛苦地、一下一下地强行吞咽!
冰冷的糊状物滑过灼痛的食道,坠入空瘪痉挛的胃袋。每一次吞咽都伴随着剧烈的干呕感,身体控制不住地抖动,眼泪混合着粘在脸上的糊糊流下。
老马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看着瓦罐里的食物随着我粗鲁的吞咽动作一点点减少。他喉咙里发出一种呼噜呼噜的、如同看着自己饲养的猪猡进食般的满意低哼。
瓦罐渐渐见底。最后一点冰冷的糊糊粘在罐壁上。我伸出舌头,机械地、麻木地舔舐着那粗糙冰冷的陶壁,试图刮下最后一点能填充胃囊的东西。冰冷的陶壁刮得舌头生疼。
终于,瓦罐空了。
我抬起头,嘴边沾满了灰黄色的糊状物,脸上泪痕纵横,混合着泥污,狼狈不堪。胃里沉甸甸的,装满了冰冷粘稠的负担,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反而加重了那种渗入骨髓的寒意和恶心感。
老马盯着我看了几秒,那浑浊的眼里似乎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玩味的残忍。他突然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黑的板牙,慢慢蹲了下来,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
“吃饱了?”他慢悠悠地问,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悠闲。粗糙油腻的手指猛地伸过来,不是打我,而是用那黑乎乎的、指甲缝里嵌着泥垢的指尖,狠狠地、带着一种侮辱性的力道,抹过我沾满糊糊的嘴唇和下巴!
“呜!”冰冷的、带着浓烈污垢气息的触碰让我猛地一缩。
他把那沾着我口水、眼泪和食物残渣的手指举到自己眼前,浑浊的眼睛盯着上面粘稠的混合物。然后,在死寂的仓库里,在我惊恐绝望的注视下,在那老妇人漠然的旁观中——
他把那根肮脏的手指,缓缓地、带着一种如同戏弄猎物般的慢动作,塞进了他自己那张喷着臭气的嘴里!
“啧…”他用力地、啧啧有声地、如同品尝什么美味般,吮吸着自己的手指!浑浊的眼睛却一直死死地盯着我,带着一种赤裸裸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兽欲和施虐般的快意!
“嗯…沾了点‘小母狗’的口水,”他啜吸着,含糊不清地咕哝着,声音粘腻如同毒蛇,“味儿……还不错。”
他将吸吮干净的手指抽出来,湿漉漉的,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令人作呕的光。他的目光,像最肮脏的爬虫,黏腻地从我沾满污物的脸,缓缓下移,扫过脖颈上青紫色的淤痕、新鲜的抓痕,在他黏腻浑浊的目光下,似乎重新燃烧起来。那目光如同带着倒钩的舌头,缓慢地、碾过敏感的锁骨沟壑,停留在我胸前那件被撕扯得几乎无法蔽体的薄薄衣衫上——残破的布料湿漉漉地紧贴着皮肤,勾勒出下方纤细的轮廓和因寒冷而挺立的顶端。冰冷的空气仿佛成了他目光的帮凶,让那两点无助的凸起更加明显。
他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含混的、如同野兽餍足般的咕噜声。
“啧……”老马慢悠悠地站起身,巨大的阴影在地上延伸,彻底将我笼罩。他不再看我惊慌失措的脸,那双浑浊的眼睛转而盯上了角落那堆散发着浓烈霉味的稻草垛。他踱步过去,粗壮的手指在发黄干枯的草茎间扒拉着,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挑选最趁手的工具。
仓库里死寂无声,只有稻草被翻动的声响,还有我无法抑制的、牙齿打颤的咯咯声。每一次呼吸都扯着下身的伤口,像有锯子在来回切割。
终于,他抽出了一根特别长、特别粗硬、带着明显韧性的干草绳。那草绳灰扑扑的,打着卷,边缘粗糙得像带着无数细小的锯齿。他用力抻了抻,草绳发出干燥紧绷的“嘣嘣”声。他似乎很满意这根绳子的强度,拎着它,不紧不慢地走回我面前。
他高大的身影再次蹲下,投下的阴影几乎将我完全吞噬。他身上那股混合着猪粪、劣质烟草和隔夜酒气的恶臭,随着呼吸扑打在我的脸上,令人窒息。那双布满污垢、指甲缝里嵌着黑泥的大手,捏着那根粗硬的草绳。他没有立刻做什么,反而像在欣赏一件什么艺术品一样,用那根冰冷粗糙的草绳末端,轻轻地点了点、拨弄了一下我胸前的布料——那片早已失去遮蔽作用的、湿冷的、薄薄的残布下,单薄的隆起正在剧烈颤抖。
“大城市来的‘小母狗’……”他沙哑的声音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玩味,草绳粗糙的末梢像毒蛇的信子,在那颤抖的凸起周围若有若无地划着圈,“皮肉是细嫩……不像村里的,糙得跟老树皮似的……”
冰冷粗糙的触感透过湿透的布料摩挲着极度敏感的顶端!那感觉像无数根生锈的细针在刺扎!身体猛地向后蜷缩,却被身后冰冷的墙壁和地面的泥水阻挡,无处可逃!
“呜……别……”破碎的呜咽不受控制地从喉咙里挤出,带着浓浓的恐惧和绝望。眼泪再次汹涌而下,冲刷着脸上的污垢和食物残渣。
“别?”老马浑浊的眼珠一瞪,咧开嘴,露出那口黄黑的板牙,笑容狰狞而残忍,“老子花钱买了你,你浑身上下,哪一块肉不是老子的?”他手里的草绳猛地翻飞起来,动作粗暴而精准!
他根本没去解那早已残破不堪的衣襟——那薄薄的布料在他手中如同朽烂的纸片!只听“刺啦”一声令人心惊的裂帛声!
胸前陡然一凉!
最后一点可怜的遮蔽被那只肮脏的大手连同那根粗硬的草绳一起,彻底撕开!冰冷的空气如同无数把钢刀,瞬间刺透了赤裸的、布满淤痕和昨夜抓痕的胸脯!昨夜被粗暴揉捏吸吮的乳尖,此刻彻底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在恐惧和寒意中可怜地瑟缩、战栗、挺立着,呈现出一种被过度蹂躏后的、充血般的深粉色,像两朵被风雨摧残得即将凋零的花苞。
“啊——!”赤裸暴露的瞬间,如同被剥光了所有保护层的贝壳,最终的内里被粗暴地展露在捕食者面前!极致的羞耻和冰冷的刺激让身体爆发出剧烈的颤抖!我本能地弓起背,双臂死死地环抱在胸前,试图遮挡那暴露的、脆弱的部位!
“挡?”老马嘶哑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嘲讽和不耐。他那只空着的、同样肮脏的大手如同铁钳般猛地探出!粗糙的手指如同烧红的烙铁,一把死死钳住我的两只手腕!巨大的力量瞬间粉碎了那点可怜的遮挡意图!他粗暴地向外一分,再猛地向头顶方向狠狠一拧!
“呃啊——!”腕骨被巨力拧转的剧痛和锁骨被拉扯的刺骨感让我失声痛叫!身体被强行拉直、向后反弓!赤裸的胸膛再无遮拦地被迫向前挺起,完完全全地暴露在他那双充满兽欲和施虐快感的浑浊眼睛里!
那两朵在寒冷空气中无助颤栗的、带着昨夜伤痕的蓓蕾,此刻成了他目光的中心点。
“老子花钱买的,就得让老子看个够!摸个够!”他咆哮着,唾沫星子喷溅在赤裸的皮肤上。那只抓着草绳的手毫不停顿!他熟练地将那根粗糙冰冷的草绳在手腕上紧紧绕了两圈!绳子上微小的倒刺刮擦着敏感的皮肤,带来一阵阵尖锐的刺痛!
接着,他根本没做任何准备,也完全没有顾及那脆弱器官的状态——那根粗硬冰冷、带着草茎毛刺的绳索,被他用极其粗暴的力道,猛地勒压在了挺立的顶端!
“唔——呜——!!!”
一声变了调的、混合着极致痛楚和惊恐的呜咽猛地从喉咙深处迸发出来,又被剧烈的呛咳打断!那根本不是抚摸,是酷刑!冰凉的触感像毒蛇缠绕,随即是火辣辣的、如同被无数细小砂纸疯狂打磨般的剧痛!绳索粗糙的表皮狠狠摩擦着那最为脆嫩敏感的凸起,勒压的力道几乎要将它碾碎!更可怕的是,绳索表面那些微小的、如同锯齿般的纤维倒刺,每一次摩擦都像是无数根烧红的针在反复穿刺!痛楚瞬间沿着神经直冲脑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