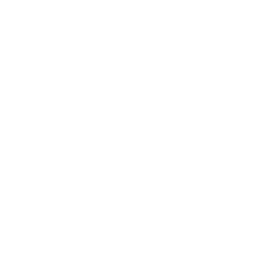第57章
深夜时分,景平城中。
寒风如刀,城中一角的丁府后院,悄无声息。
一扇隐秘小门缓缓开启,一道灰影贴着墙根潜出,脚步极轻,仿佛连地上的霜雪都不敢惊扰。
他穿过曲折回廊,避过巡夜的更夫与城防兵影,顺着一条无人小巷一路钻进丁府最深处的密室——
那里已点亮了昏黄的油灯,灯芯极细,火光跳动如豆。
密室里站着两名黑衣人,脸蒙黑布,目光如刃。
“确认了吗?”其中一人低声问。
“西门守兵已换,今夜子时前,巡逻薄弱。”
另一人冷声道:“你丁家真敢赌。”
“不是我们敢赌,是你们的大王敢赌。”那丁氏家丁冷笑一声,取出一枚铜符,其上犬戎狼头浮雕清晰可辨。
“开门的条件,犬戎许了吗?”
“许了,攻破城后,西市以西,归丁家。”
“尸山血海换半城……你丁家真会做买卖。”
丁氏家丁不语,只是点头。他手指颤了一下,低声道:“走。”
三人同时扑灭灯火,翻出窗去,消失在夜色中。
……
寂静西门,一片死寂。
此时早已过了三更,守门的士兵早换了两轮,岗哨稀薄,灯笼昏黄。
“开门。”一名丁氏的家丁走上前,从袖中掏出一支火折,划亮,在黑夜中一闪即灭。
数息后,门缝中探出一个黑影,低语一声:“确认身份。”
铜符递出,火光再起。
对方不再言语,转身而入,数名黑甲“守军”将门内横木拔开,沉沉木门在夜中缓缓开启,露出一道缝。
一缕冷风灌入,随后是一阵沉重的马蹄声,从门外的黑暗深处传来。
犬戎先锋,入城了。
几乎同时,城中多处民宅仓库起火,浓烟翻腾,火光染红夜空。有人惊呼:“失火了!是火!”
紧接着,街头巷尾传来惨叫与兵刃交击声,夜色骤然变得嘈杂。
……
西南角一处驿馆,惊醒的百姓赤足奔出,满脸惶恐。
街头几个兵卒闻讯赶来,却在转角遇上快速突入的犬戎兵,一刀一剑,喉断血涌,转眼倒地。
守兵军心本就松弛,如今见火光、闻惨叫,不知敌从何来,惊慌四散。有人跌跌撞撞跑回军营,高声大喊:
“敌人进城了!敌人攻进来了!”
军营霎时如锅中热油沸腾,许多人更衣不及,惊慌奔逃。
……
府衙内,陈载仁方在后院歇息,床帷尚未放下,便听得外头喧哗:“失火了?怎会有哭喊声?”
丫鬟尚未来得及回报,院外已乱成一团。婢女惊叫、内眷呜咽。
“快!来人!”
这时外头传来老仆疾奔之声:“大人!西门……西门已失守!犬戎杀进来了!”
“什么?”他声音都在颤,“怎么会……”
陈载仁披衣而起,脚下打滑跌坐在地。他挣扎起身,扑向案头,那上头摆着一份尚未封蜡的文书,正是他与士绅密谋写下的降书。
“原是明日清晨送出的……”他喃喃,捧着那纸,指节发白,“可如今,献城之功,怕是没了。”
他双手发抖,几欲将那文书撕碎。
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那些士绅中,怕是有人根本不想等到明晨!
……
绥宁副都统高彦清正在中军大帐小憩,突闻急报赶至。未待更衣,便策马直奔西门最近的营房。
高彦清飞身下马,长靴踏进军营,夜风裹着远处的火光吹得营门猎猎作响。
他怒目环顾,怒声喝问:“营中值守将官何在?西门失守,为何不战而退?”
无人应声。
营地空旷得近乎诡异。
营帐内烛火东倒西歪,有的还在晃,有的已经熄灭。
甲衣横陈,兵器散乱,连箭壶都倒在地上,一脚就能踩上去——像是突遭劫掠后的残垣断壁。
他疾步冲入主帐,眼中血丝暴涨,只见几名值夜士兵衣衫不整,正狼狈从角落钻出,一见他便吓得瘫软跪地。
“逃了?”高彦清声音冷得像是从喉骨中挤出来的,“你们一个个,连甲都没穿,连兵刃都没拿稳……逃到哪儿去?!”
“将军……”一人哆嗦着,“敌人太猛……我们……守不住……”
“守不住你便丢了甲?!”高彦清怒吼一声,声音如雷霆滚过营帐,“你们手中的兵器是木头做的么?!犬戎铁骑杀入家门,你们连一刀都不敢挥,就只会逃?!你们是士兵还是豢养的狗!”!”他转身走出营帐,眼看外头更多士卒正抱头鼠窜,甚至有人翻墙出营。他猛地拔剑,剑锋发出清啸,映着火光寒光凌厉。
“你们逃得过这座城?逃得过那十万犬戎的刀下?”
“你们想弃家弃子?还是想让他们死于敌军屠刀之下?”
无人回答。
风更冷了,远处西门的火光已烧得天色微红,仿佛整座城都要陷入血海。
高彦清双目赤红,望着这些连抵抗都不敢尝试的兵卒,一股难以名状的痛意从心底迸出。
他颤着唇,像是要咆哮,却忽然哑声低喃:“算了……景平,已完。”
他仰天长叹,血气翻涌,忽而将剑横在颈前,双膝跪地。
“此身既无力保一城百姓,便当以死谢罪。”
话音未落,他已手起剑落,剑刃寒光在火光中一闪,朝颈侧削去——
“将军不可!”
副将陈弼冲上前来,一掌拍飞他手中长剑,铁器跌落地面,发出一声刺耳的铿锵。他跪倒在地,泪声俱下:“将军若死,这城就真的完了!”
高彦清喘息如牛,颤着手跪在地上,久久未语。火光映在他泛红的眼睛里,仿佛淬了血的火焰。
“我宁可……与这城共亡。”
陈弼死死拽住他:“主将之责,是撑到最后一刻,不是第一个倒下!”
“有援军…来援军了!”
不知是谁一声喊,像从夜色中穿透火焰飘来,带着不真实的震动。
破碎的街巷,惊惶的逃兵,甚至惊恐哭泣的百姓都抬起了头。
下一刻,他们看到了。
火海尽头,千余黑甲兵从夜中奔来,雪地上踏出一道血线。
最前头一位黑甲将校,脸上血迹斑斑,嗓音带着撕裂的沙哑,像是咬着命从喉咙里吐出来的:
“城门未塌!景平未死!我季崇还在——谁敢退一步,我便一刀劈死他!”
他高举着长枪,那枪头挑着的,不是旗帜,而是一个人头。
那是丁氏家的管事,被他生生砍了头、斩下奸通者的罪证。
那一刻,所有人都看见了:
那支千人的部队,从火光中杀来时,没人喊“救援”,也没人吹号角。
他们穿着杂乱的甲,步伐却整齐如一。他们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在看到西门已破时,齐齐加速,如同一支黑色的利矢,逆着逃兵潮水冲去。
犬戎部队正在横扫街道,马蹄碾过尸骨,血水流淌如河。可这些人,却从正面撞了上去。
不是侧击,不是偷袭。
是正面冲锋。
是以血肉之躯,逆撞铁骑。
没有任何战术,没有半点犹豫。他们就那么直直地冲了上去,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冲就是死。
那一刻,仿佛整个景平都停了。
因为没有人退。
那一千人,在最狭窄的巷口,最混乱的街市,和最濒临崩溃的西门前,寸步不让。
一个倒下,另一个顶上。
两个倒下,后面三个扑上来。
有人被马踏开了肚子,却依然抱住敌骑的腿,用尽最后一口气咬断了马缰。
有人腹部中箭,肠子滑出半截,依旧死死挡在门轴下,只为了等那扇门重新关上。
他们没有退路,也不需要退路。
他们是来——以血肉填门。
那支千人的部队,自始至终,没有一个逃兵。
哪怕犬戎围杀得人仰马翻,他们依然寸步不退。
犬戎已经入城,可他们仍一声不吭地往前杀,像黑夜里的火炬,哪怕灭了,也要照着后人一眼。
四面八方,那些躲着、退着、哭着的人,终于看呆了。
有个士兵坐在断瓦后面,缩成一团,浑身哆嗦,他咬着指节,一直不肯看。但他听见了,一声声喊杀声中,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吼:
“刘铁柱!你不是说,要回家娶翠花的么!来啊——你就这么活着,让翠花给犬戎当奴吗!”
他猛然抬头,看见他的兄弟,正在火光中倒下,喉咙被穿透,却依然拖着犬戎一兵扑向地面。
那声音在他脑子里炸开——
“你们真的看得下去?!”
这一声不是谁喊的,而像是从天地间逼出来的。
周围的溃兵都在颤抖,脸红,眼红,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再逃。
不知是谁,握住了手中丢掉的刀。
不知是谁,第一个站起来,像一头被捶醒的兽,转身朝着火光冲去:
“爹娘教我做男人,我不能像狗一样活!”
“那帮兄弟都上去了,我们还缩着?还活着干嘛!”
“我是人…… 我不要做犬戎的狗!!!”
人群像沸水,一点点开始冒泡。
然后,轰的一声,整座营地炸了——是士气被引燃了。
那些一度逃跑的兵,纷纷拔刀扔盔,甚至有人光着脚、手中血淋淋地攥着半截断枪,大吼一声:
“冲啊!老子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夜色中,战鼓未响,喊杀声却自城中潮水般奔腾而起。
那一刻,整个西门被点燃的,不是火,是血。
…….
西门外,犬戎大股骑兵已逼近,前方斥候飞骑来报:“西门已控,我军先锋部队已入城屠杀。”
卓禄一听,嘴角微勾。
“景平不过一夜而已。”
战鼓擂响,牛角声呜呜直震耳膜。黑色马队排成疾阵,呼啸而来,如浪卷千军,势不可挡。
但当他们来到城门前,眼前却是一道紧闭的巨门。
“怎么回事!”卓禄一勒战马,怒喝,“门呢?!”
“狼王!”斥候面色苍白,“西门……被重新夺回了!”
“放箭!!!”卓禄愤怒之极,振臂高呼。
转眼间,万箭齐发。
犬戎怒射如雨,遮天蔽日,箭矢密集得几乎看不见夜色的天幕。尖锐的啸声仿佛万鬼哀号,齐齐扑向那扇刚刚关死的西门。
但城门坚闭如铁。
箭矢如骤雨打石,“叮当”之声不绝于耳,金铁交鸣,激烈而绝望。
木箭断,铁矢弯,箭头深深嵌入门板、射进砖缝、溅起碎屑,但门后没有一丝回应。
没有士兵探头,没有弓箭回射,连一句叫骂都没有。
那扇门就像死了一样,却又像活着一般,用沉默狠狠掴了犬戎一耳光。
唯有从城内传出隐隐的金戈刀鸣——那是景平人在一寸一寸绞杀入城的残敌。
———
大通铺内的大战也还在继续,姜洛璃已然翻身跨坐在王二喜身上,她的细腰如柳枝般起伏,雪白的肌肤在昏暗的月光下泛着暧昧的水光,仿佛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诱人得让人移不开眼。
她脸颊泛红,汗水顺着脖颈滑下,落入那深邃的乳沟间,被王二喜的双手包覆揉弄着,每一次挤压都让她发出一声声被压抑的低吟,那声音如泣如诉,带着一丝不甘的媚态。
王二喜躺在那里,任由她主动上下起伏,他眯着眼,看着她一边骑着自己,一边咬唇忍喘的模样。
那副快感到极致还死撑着不肯叫出声的倔劲儿,反倒叫他更兴奋了。
他的手掌一把抓住她胸前那两团柔软,揉得狠了些,指尖嵌入肌肤,留下淡淡的红痕。
姜洛璃的身体随之颤动,她的下身紧紧包裹着他,每一次下压都发出黏腻的水声,像是夜色中的低语,充满了原始的诱惑。
被子早已滑落,整间屋子只剩肉体碰撞间那黏腻的水声与她嗓子深处一声声喘吟,在夜色里透着一股香艳到极致的媚态。
她的臀部圆润而饱满,随着动作摇曳,汗珠在上面滚动,像珍珠般晶莹。
她下压得重了些,腰下猛地一颤,偏还强撑着身子,喘着气俯下身,小手往后探去,轻柔揉捏着他的囊袋,指尖灵活得像在调情,动作又贱又媚。
那指尖的触感如丝绸般滑腻,轻轻按压、旋转,带着一丝挑逗的温度,让王二喜的呼吸瞬间乱了节奏。
他重重顶了几下,顶得她整个人都伏倒在他胸膛上,眼角含水,喘息凌乱,却又像猫似的贴着他,身体的曲线完美贴合他的轮廓。
她的发丝散乱,贴在汗湿的额头,散发着淡淡的女人香。
然后,她俯身贴上他的唇,起初只是轻轻一触,像蝶翼掠过水面,浅浅试探,柔得几乎没有重量,却让他一瞬屏息。
她的唇瓣温热而柔软,带着一丝果实的甜腻,轻轻摩挲他的下唇。他能感觉到她呼出的热气拂过他的脸颊,带着隐隐的湿意。
她的舌像是带了勾子的,悄无声息地绕住他的,在他口腔里游走打转。
她不急着缠紧,而是一点点描摹他的上颚、舌面,像在舔一颗糖,又像在施某种慢性蛊术,一寸寸引他沉沦。
那舌尖的触感湿滑而灵巧,每一次滑动都像是电流般刺激着他的神经,让他不由自主地回应。
她甚至故意含住他的舌尖,轻轻一吸,舌根又抵着他舌侧摩擦——那动作太细腻,太暧昧,仿佛在把他整个人都含进身体里去。
那种缠绵、那种温热和湿滑,把他吻得五感全乱,思绪像被溺在了甜腻中,只剩下身体对她的本能回应。
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抱紧她的腰肢,指尖嵌入她的臀肉,感受着那柔软却富有弹性的触感,仿佛每一寸皮肤都在回应他的渴望。
姜洛璃的身体微微颤抖,她一边亲,一边缓缓调整角度,贴得更紧,像是要把两人整个人都吻进彼此灵魂里去。
唇舌之间已分不清谁在主动,谁在索取,只剩黏腻的水声,像是情欲深处发出的呢喃。
她忽然轻轻一哼,像是也被这场吻弄得意乱情迷,然后猛地加深了这个吻,舌尖缠住他,灵巧地绕了一圈,勾住不放,像猫勾住猎物的尾巴,湿热中透出一点狠劲儿。
她吻得太认真,太投入,仿佛世间只剩这一口气、一点温存。
她的舌头在王二喜的口中肆意游走,每一次摩擦都带来阵阵酥麻的快感,让他不由得低吼出声,那声音闷在喉咙里,像野兽的喘息。
姜洛璃的双手也不闲着,她轻轻抚摸着他的胸膛,指尖划过他的皮肤,留下轻微的红痕,像是标记着她的领地。
王二喜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只剩下对她的渴望,他用力回应着这个吻,舌头与她的纠缠在一起,交换着彼此的津液。
等她终于松唇,唇角还牵着一丝银亮的水痕,呼吸轻颤,眼神迷离得像被爱欲浸透的琉璃。
她伏在他胸口,舔了舔自己红润湿润的唇瓣,喃喃低语,媚声入骨:“这回……伺候得你还满意吗?小狗狗。”
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丝调侃的意味,却又充满了诱惑,让王二喜的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他看着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里面闪烁着满足和挑逗的光芒,仿佛在邀请他继续这场游戏。
就在这时,大通铺内传来一阵细微的动静,有人翻身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
那人似乎在梦中呓语,声音模糊不清,却带着一丝淫秽的意味,仿佛正在梦里玩弄女人,喃喃道:“嗯……骚货,别跑……让我好好疼你……”
那声音断断续续,带着粗重的喘息,在安静的屋子里回荡开来。
姜洛璃闻言,轻笑出声,她转头瞥了一眼那方向,然后回过头来,对着王二喜眨了眨眼,脸上绽放出一种调情的笑容。
她的臀部开始不断扭动,圆润的臀肉在王二喜的下身摩擦着,每一次扭动都像是故意在撩拨他的神经,让他的欲火熊熊燃烧。
她轻轻扭动着身体:“他们只能在梦里幻想,而你,却在这里,真刀真枪地操我,小狗狗,你看你憋得脸都红了……来吧,别忍着了,射给我啊……”
她低声呢喃,唇角带着几分挑逗,“别再忍了,把你的温热全都给我吧……让姐姐的体内满满都是你的一部分,好不好?”
王二喜强撑着身子,咬紧牙关,不想这么快就缴械,他喘着粗气,低声回应:“不行……想让我这么快就完了?..你休想”但他的声音已经有些颤抖,身体的本能在她的撩拨下开始崩溃。
姜洛璃见状,她俯下身,胸前的柔软紧贴着他的胸膛,臀部继续扭动得更猛烈些,像是故意在加速他的崩溃。
:“别忍了嘛~~,小狗狗……姐姐知道你想射……,射出来,让姐姐感觉你对我的爱意……”
她的气息热乎乎地喷在他的耳廓上,带着一丝湿润的潮意,让王二喜的意志力如堤坝般崩塌。
他用力抱紧她,腰部猛地向上顶撞,每一次撞击都发出啪啪的声响,混合着黏腻的水声,在屋子里回荡。
就在这时,又一个声音响起,有人似乎想撒尿,迷迷糊糊地从铺位上爬起,那人揉着眼睛,嘟囔着:“憋不住了……”
他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准备往屋外走,却忽然听到房间中传来女子的声音,那娇媚的喘息和低吟,让他瞬间清醒了几分。
他停下脚步,借着昏暗的月光,看到了王二喜的铺位上趴着一具曼妙的身姿,那曲线玲珑,雪白的肌肤在夜色中隐约可见。
他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但紧接着又听到一声娇吟,他顿时大叫一声:“娘们!这里有娘们!”
他的叫声如惊雷般炸开,整个大通铺瞬间被吵醒。
其他汉子们纷纷从睡梦中惊起,揉着眼睛坐起身来,有人还迷糊地问:“啥?娘们?哪里来的娘们?”
王二喜心头一惊,他急忙一把将姜洛璃拖倒在身边,抓起滑落的被子,慌乱中盖在两人身上,试图遮掩住这香艳的一幕。
那人还在大叫:“大家伙儿,快看啊….那骚娘们爬到二狗子铺上挨操着!”他的声音兴奋而粗鲁,带着一丝嫉妒的意味,瞬间点燃了屋内的气氛。
房内蜡烛被点燃,几盏昏黄的烛光亮起,照亮了整个大通铺。
汉子们纷纷围拢过来,有人揉着眼睛,有人已经露出了猥琐的笑容,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王二喜的铺位上。
姜洛璃被王二喜紧紧抱在怀里,被子下她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脸颊贴着他的胸膛,心跳如擂鼓般加速。
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如狼似虎地扫视着他们,那种被窥视的刺激让她下身不由得一紧,夹住了王二喜的硬物,让他忍不住低哼出声。
王二喜的脸色铁青,他试图掩饰:“你们瞎嚷嚷啥?这哪有娘们!”但他的声音有些虚弱,底气不足。
姜洛璃的手悄悄伸向王二喜的下身,继续撩拨着他的囊袋,指尖灵活地按压着,让他全身一颤。
她低声在王二喜耳边道:“小狗狗,快射啊……在他们面前射给我……证明你占有了我…”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兴奋的颤意,仿佛这种暴露的刺激让她更加欲火焚身。
那发现的人大笑起来:“哈哈,王二喜,快掀开被子,让弟兄们瞧瞧,这骚货是谁?这般不要脸,竟敢跑这里来了!”其他汉子们也附和着,有人吹起口哨,有人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仿佛随时准备扑上来分一杯羹,那口哨声尖利而下流,混合着粗重的喘息。
王二喜猛力挺身,被子不断起伏,一人见他居然在自己眼皮底下又干起来了,上前一把拉开被子:“操你娘的二狗子,独吞这骚货,老子也要尝尝!”
那人骂骂咧咧,声音如雷鸣般粗野,被子被猛地扯开,露出了两人纠缠的躯体。
姜洛璃双手遮面,下身刺激的收缩,王二喜被暴露的刺激下猛地一颤,热流喷涌而出,射了进去,那射出的瞬间如火山爆发,让他全身抽搐。
姜洛璃高声浪叫,那叫声娇媚而放荡,回荡在屋内:“啊……好热……小狗狗,你要护着姐姐哦!”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媚骨的颤抖,耳边全是男人的肆意眼光,那些目光如刀子般切割着她的皮肤,让她全身发烫。
女子的裸体看呆了众人,他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雪白的肌肤、丰满的曲线,那目光中满是贪婪和淫欲。
王二喜退出阴茎怒吼一声,拳头如铁锤般砸出,硬生生踹飞了两个凶徒,吼道:“姐姐快跑!”他护在姜洛璃身前,身上被男人们彻底暴露,精液顺着腿间滑落,黏腻而温热,在烛光下散发着淫靡的光泽。
有人盯着姜洛璃两腿间残留的血迹,嗤笑道:“这丫头刚破瓜,血迹还没干,鲜嫩得很,弟兄们快上!”
紧接着又传来一阵阵肮脏的叫嚣
“操,还真是个雏儿,头一回就选在我们男人铺上开苞,贱得这么彻底的我头一回见!”
“看那腿夹得,还想夹住点儿残羹剩汁?放心,待会儿给你换新鲜的灌!”
“妈的,这种骚货上哪儿找去?敢当众被人玩,天生的娼胚!”
“别抢,咱们一个一个干进去,她巴不得咱慢点玩,她好好享受!”
“谁带绳子了?绑床上慢慢干,省得她又夹又拱,一身骚劲儿勾得人蛋疼!”
“妈的!这贱货处女居然给了二狗子?她眼瞎了?这么个下脚料也配吃头道汤?!”
“这么水灵的货,被那废物捅开了!她是成心贬低咱们是不是?当着我们一屋子爷们儿,非他妈给最废的那个开苞,老子气不过!”
“今天不把她干翻在地上轮一圈,我心里这口气他妈咽不下去!你们说是不是?二狗子都能开苞,我们难道白长了这身肉?”
姜洛璃捂着脸,一脸羞红地用手臂推开王二喜的护卫,也一脚踹飞一个朝自己扑过来的人。
“我看到她的屄了,阴毛这么浓密,一看就是个骚到极致的荡妇,老子今晚要操死她!”有人一脸兴奋的大叫
男人们淫笑着,声音杂乱而下流,有人伸出手摸向她的屁股,那粗糙的手掌用力一抓,留下红印,让她娇吟一声;有人抹向她的胸膛,指尖捏住乳尖,粗暴地揉捏,激起她身体的颤栗;还有人摸上她的大腿,沿着曲线向上滑,带着热乎乎的掌心温度,让她下身一紧,那淫笑声如狼嚎般回荡:“这小屁股真翘,摸着就硬了!”“来,让老子舔舔这破处血,哈哈!”整个屋子充斥着他们的喘息和笑骂,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男人气息,刺激得姜洛璃的心跳如狂风暴雨般加速,她既羞耻又被这混乱的触碰点燃了隐秘的快感。
王二喜被死死摁在地上,几个壮汉压住他的四肢,拳头雨点般落下,他挣扎着大喊:“你们这些畜生,放开我!”
姜洛璃不断躲闪,踉跄着跑了出去,那羞红如朝霞般烧灼着她的脸颊,脚步慌乱却迅捷
男人们追了出去,骂骂咧咧地吼着:“别让那骚货跑了!”可是姜洛璃跑得很快,一溜烟没了影儿,只留下夜风中她的喘息和远去的脚步声,消失在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