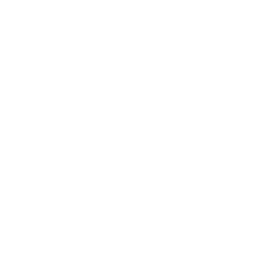第48章 罗马城
进城前,维修斯看到一条高耸的水道桥(Aqueduct)从远处穿进城里。
为了从远处的山上运水过来,水道桥的设计具有非常微小的坡度(大约每千米下降1米),这是要求极高的精确度。
水送进进城后,再通过铅管送到一个个喷泉取水口,造就了自来水。即便是两千年以后,也不是什么国家能造出精度这么高的工程。
按当下的科技、生产力来说,这套自来水系统简直就是开了挂,也是罗马城能容纳近百万人口(75万)的关键之一。
(罗马古城占地大约20平方公里,就一个中型乡村的大小,连小镇的规模都达不到。人口密度达3.75万人/平方公里,与之对比上海虹口区2.9万人/平方公里。)
罗马人是这个时代的基建狂魔,每一座雄伟的建筑,都是设计师的心血和无数奴隶的血泪铸就。
他们进城时,守卫盯着维修斯看,但看到他脸上每天让卡米拉割一条的伤口,就忽略他了。
这说明元老院已经知道他要来了。
罗马——七丘之城,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近百万。
罗马——噬人之城,不管往这个城市注入多少人口,第二年都不会超过百万。
仿佛一只无形之手控制着这座城市的人口,而冬天就是它爪子最锋利的时候。
他从马尼亚嘴里听了很多遍罗马的样子,现在一看,见面不如想念。
台伯河的暴涨,让罗马的低洼处全都泡在水里,粪便、死耗子就在水面上飘荡。有些人手上举着篮子、衣物,赤裸着身体淌水而行。
马尼亚说罗马城有连通的下水道,但到了冬天就失灵。
岂止是失灵,他们路过一间公共厕所时,臭气从里面喷出来。
公厕里发出风的啸叫,以及咕噜咕噜的液体翻滚声,就像一个消化不良的巨大怪物,或是一座愤怒的火山,让人担心它会随时喷发。
整座城市都笼罩在难闻的臭味中。
这座拥有天量人口的城市十分拥挤,除了他们行进的大道比较宽,分支的街道就三四米宽。
建筑之间紧紧挨着,有的小巷不足两米,两座建筑的人从窗户探出身子就能握手。
路两边叮叮当当的工匠、叫卖的商贩、爬行的乞丐、随时准备转化成扒手的孩子,加上头顶着篮子、陶罐、背着麻袋、牵着牲畜的人流,令人感到十分的压抑、烦躁。
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肉眼可见的差,皮肤病随处可见,各种肤色、种族的行人呈现出某些病态。
“你之前来过罗马吗?”维修斯抬头问骑在肩膀上的卡米拉。
“很小的时候。”她说。
从她抓着他头发的力度可知,她很紧张,她的双脚扣在他腋窝下,避免接触到行人。
回头看一向话唠的诗人,他和娈童也是满脸的紧张,手紧紧按在放钱袋的胸口。
“我是卢基乌斯·佩蒂乌斯·马克西姆斯的奴隶,我是卢基乌斯·佩蒂乌斯·马克西姆斯的奴隶。”
维修斯向喊声看去,是一个顶着篮子的女奴边走边喊。
女奴上身的袍子坠在腰间,身上鞭痕累累,与其说是人的皮肤,倒更像是花豹的皮。
向人展示遭受的虐待,大概是她唯一能对抗主人的方法。
看路牌,他们的左边是阿文蒂诺山,因为也就四五十米的海拔落差而已,其实还是叫丘比较合适。
据马尼亚说,这里是平民的聚集地。
山上的公寓还好,低洼处的公寓已经泡在水里,有人驾着小船做起了摆渡的营生。
“还有吗?还有吗?一枚铜币送进台伯河。”一个牛车夫叫嚷着。
牛车的车板上堆着几乎枯瘦的尸体,老人、女人、小孩都有。
“维修斯,那边有集市,我去把骡子卖掉。”诗人说。
“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各走各的路吧。”他扛着卡米拉向前走。
“不不不!我们的缘分远没有到尽头。”诗人着急地冲向集市。
继续向前走,根据路标,他知道自己在阿文提诺山与帕拉蒂尼山之间。
一座很长的巨大建筑出现在眼前,马克西姆竞技场。
按马尼亚所说,他的前身在这里搏斗,然后一道雷劈中,他的灵魂就是在这里穿越过来了。
此时竞技场并没有表演、比赛,门关着,他就在附近慢悠悠地转,然而,该死的天气又下起雨来了。
他把卡米拉拎起来,把她绑在身上的皮带套在脖子上,把她收回牛皮披风里面。
“急迫使人愚蠢,而愚蠢常以铜钱为代价。但愿买家因为少花了铜钱的缘故,让骡子少挨一顿鞭子。”卖掉了骡子的诗人气喘吁吁地赶过来,懊恼地说:“我本要投靠父亲的老朋友,可我刚刚在集市打听,他已经在内战时死了,愿诸神保佑他的子嗣。命运女神捉弄我这样渺小的凡人。现在我得找地方安身,如果你们也还没处落脚,何不继续结伴呢?”
“你于我无用,诗人,别跟着我们了。”他对诗人说了,继续往前走。
“我很有用,正是因为我太有用了,所以才让你感受不到,就像你的胃不生病时,你就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或是像一头老实犁地的勤恳水牛,让你以为田地本该那样。你知道吗,我正要给我们寻找一个住处,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稍稍等待,就能有地方可以躺下休息。”诗人跟上来说道,他指着右前方的一座公寓说:“那里,我就要在那里给我们找一个住处。”
那座公寓在帕拉蒂尼山的山脚,地势稍高,不受洪涝的影响。
这里的建筑明显比阿文提诺山的高档一些,除了公寓,有很多二层的别墅,街大约4米宽,蜿蜒向上,街的两边开满商铺,很嘈杂。
所谓的公寓,在维修斯看来,就是底层作为商铺、楼上作为住宅的筒子楼。
在一排商铺的中央有个楼梯,走上去就是一个平台,是筒子楼的中心,头顶上一方天井就是这里的唯一采光。
上面走廊边,有些人借着这昏暗的光在干活。
他把卡米拉放下来。
一股尿味在弥漫,是楼梯角落里有一个皮匠公会放置旳大陶缸,用来收集尿液做硝皮用途。除了尿味,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霉味。
楼梯边上有个桌子,一个拉丁男人正在蜡板上记录。
“你是收租人吗?”诗人问。
“是。”收租人把他们打量一番,问诗人:“你是骑士?”
诗人拍拍托加袍上的红边,有些骄傲地说:“正是,我来罗马竞选财务官,现在要找个居住的地方。”
“住大间吧,大间才符合你财务官的身份,只要每月4枚金币。”
“带我们看看,再做决定。”
收租人拿钥匙打开了角落的房间。
经常干土木造房子的读者都知道,建筑角落的房间都大。
这是一个两居室,客厅一张小床、一个桌子四把椅子、一扇窗,里面的卧室一张大床一个柜子。床上没有床垫床套,是个空架子。
按工匠的收入换算,这间没有卫生间的二居室每月要人民币三万多,不愧是首都啊。
诗人拉收租人进卧室里小声地讨价还价,试图通过贿赂降低租金。
维修斯和卡米拉在客厅的窗户向外看,天色已经渐黑了,今天就在这里落脚吧。
诗人以每月给收租人12枚银币的贿赂,以3枚金币的月租租下了房屋,签订合同交了钱后,收租人给了一把钥匙。
维修斯和卡米拉都着急要吃东西了,所幸楼下就有食肆。
“就像我说的,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在这里慢慢吃,我和尤文提趁天黑前先去买床单、毯子和其它用品。”诗人说。
“嗯。”
“给我4个面包、两碗麦粥、两只烧鸡。”他点菜。
“哪种麦粥?”厨子的女人指着两个不同的桶问。
真是新鲜,两个桶,一个是热的麦粥,另一个是冷水泡的小麦,她问要哪种?
“热的。”
“4枚银币。”
首都的物价真是贵,这么一顿就要吃掉一个工匠4天的工资。
卡米拉哗啦哗啦地在装满金币的钱袋里翻找,凑出4枚银币付账。
财帛动人心,厨子和几个食客盯着卡米拉的钱袋挪不开眼,不过没人敢试探维修斯的武力。
维修斯的疑惑一会就有了答案,一个分不清贫民还是奴隶的人买了一颗卷心菜、一碗凉水泡小麦,吃起来。
光是看着那人吃,都觉得肚子里拔凉拔凉。
事实上要弄清占总数70%的底层人是否奴隶,是毫无疑义的事,因为他们的处境是相同的——徘徊在生存边缘。
以自由人、奴隶这么简单的划分,来理解罗马社会的话,过于粗暴、片面。
比如:塞纳去逛街的话,阿格里真托人都要给这个维修斯床上的女奴让路。而有人是自由民,是因为连自卖为奴都没人要(疾病或年老)。
古罗马的奴隶造反并不算多,维修斯觉得主要是奴隶们(不含作为极端消耗品的矿井、火山灰等奴隶)看底层自由民的日子未必比自己好过多少,也就不迫切得到自由了。
进罗马城之前,在路上就很少能看到树木的踪影,兴许是因为柴火太贵了,以至于贫民都吃不起烹煮的食物。
他们吃饱后,维修斯把啃剩下的鸡骨头放在那个贫民或奴隶的面前,走出食肆。
回到公寓,他看到娈童尤文提在铺床,诗人卡图卢斯在摆放盆盆罐罐。
卧室的大床铺了秸秆编织的床垫,盖着亚麻床单,上面放着一张羊毛毯。
他毫不客气地上大床试试,还行吧,将就着能睡。
“罗马城的东西真贵!维修斯,我和尤文提出去吃晚餐了。”诗人把钱袋放进柜子里,只带着几枚铜、银币出去了。
门外突然嘈杂起来,他走去门口看,是一群人衣衫褴褛的人下工了。
这些人陆续在收租人的陶罐里放一枚铜币,然后进入一个房间。
让他惊奇的是,一个房间里走进去了好多人,仿佛在变魔术,这他妈是个任意门能通往另一个地方?
他忍不住好奇,走过去看,只见房间里有四排高低不等的木架子,有十几、二十个人把胸口压在木条上,站着低头垂手不动了。
这些人没有工具,有些人身上缠着绳索,让人感觉是做日工的。
这场景让他看了都有点毛骨悚然,这是搞什么呢?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问收租人。
“睡觉啊!”
“睡觉?”
“是啊。”
牛马是可以站着睡觉的,但即便是牛马,隔一段时间也需要躺下进行一会深度睡眠。
因为罗马寸土寸金,这些人就一直这么站着睡觉?一枚铜币就只配占这么点地方?
维修斯这第几年来,难得有一种恐怖、毛骨悚然的感觉。一种更系统的力量在收割着人命,远不是他的杀人效率可比的。
人群不断地涌入这幢公寓,渐渐让他担心楼会因为不堪重负塌掉。
这栋楼可能原本是三层的砖石结构,一层商铺,二三层住宅。
现在呢,从三层以上的木头梁柱可以看出,四到六层是后来又叠床架屋的木构层。
这栋楼容纳的人口,比他以为的多三四倍以上。
手上拎着工具、食物的男人们回到各层的房间,明显生活条件好一些,但似乎也是好几个人住一个房间。
女人在这栋公寓挺少的,80%都是男人。有一个长得还行的女人,和两个男人、一个小孩住在一间屋里,4平米的房间里住4个人。
不一会,诗人和娈童带着一篮子面包回来。
维修斯指着牛马们站着睡觉的房间,问诗人:“你见过这种吗?”
诗人瞧了一眼说:“我听说过。”
“他们为什么不去乡下种田?乡下的奴隶过的都不比他们差。”
“这些人就是从乡下来的,他们失去了土地,除非他们自卖为奴,否则地主也不需要他们,就来城里谋生了。”
原来是土地兼并的失地农,这些人是连床单都没有的无产者。
回到房间里,点燃一盏油灯,诗人和娈童在桌子上吃面包。
公寓里没有生火的条件,维修斯就只能将就用冷水和卡米拉擦洗。
纵然是这已经是这栋楼最好的房间,对于他来说,生活条件也太辛苦了,还是得搞套有奴隶伺候的别墅来住。
除了穿越过来的第一天他住在笼子里,之后他就一直跟着马尼亚住别墅,睡在主卧里肏女主人,真没过过苦日子。
他们脱了衣裤在床上相拥接吻,他尝着她的小嘴,听见客厅传来啪啪声和喘息声。
抬头一看,娈童伏在桌子上,诗人正在抱着娈童的屁股冲撞。
娈童闭着眼睛,张嘴呻吟着。
娈童的名字叫尤文提乌斯,尤文提是尤文提乌斯拿掉后面us的呼格,在拉丁语里是亲近之人的称呼方法。
尤文提的岁数比卡米拉还小些,屁眼却要承受成年人的鸡巴,但在这个年代里,娈童是奴隶中的幸运者了。
娈童就是中文语境下的小书童,是主人重点培养,未来会成为重要帮手的奴隶,与主人同吃同睡,生活上也不吃苦。
干娈童不光是宣泄主人的性欲,也是建立从属地位关系,让娈童从身心上都习惯性地顺从于主人。
娈童不来月经,也没有女人乱七八糟的想法,出门办事也比较方便。
所以,主人出门在外带娈童的,远比带女奴的多。
油灯的光照不到桌下的位置,但娈童必定是被肏得小鸡巴乱甩。
“亲爱的,我不流血了。”卡米拉把手伸进袍子下面,抚摸他的鸡巴。
“没干净呢。”他说。
“那你可以把我当成男孩,使用我的屁眼。”
“我肯定会玩你的小屁眼,但不是现在,你需要慢慢来,否则你会肛裂的。”
“亲爱的,你的鸡巴硬了。”她的小手撸着甜腻腻地说。
“那是因为你,我的小可爱,我想进入你的身体里。”
“我也想让你进入我的身体,因为我爱你,我亲爱的丈夫,我从未像爱你这样爱过别人。”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我知道我爱你。”
“爱就是喜欢有一个人的生活,喜欢有她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做爱、一起呼吸、一起杀人。我喜欢有你和我一起做这些,所以,我爱你卡米拉。”
“嘻~,维修斯去哪里,卡米拉就去哪里。”她欢喜地重述婚姻的誓约,钻进毛毯,握着他的鸡巴,含进嘴里吞吐起来。
鸡巴舒爽起来,在她的小嘴里更坚挺了。
他把她的身体抱在身上,用手指揉她的小屁眼和小屄,小屄变热,慢慢渗出滑腻腻的水来。
“嗯~”她边口交边呻吟,俩人相互给对方欢愉。
卡米拉小小的,才到胸口,养她就像养个女儿,她甜甜的爱恋又像清纯可人的初恋。给他一种复合的感觉,就像酸甜可口的水果。
(我只是在小说里意淫一下,而时至今天,因为爱泼斯坦案分裂的西方人权大国,居然还有36个州允许童婚。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密西西比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这4个洲不设最低结婚年龄,甚至比古罗马的最低结婚年龄12岁还要无底线。一位在教堂性侵幼女,导致9岁的女孩怀孕的神职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因为女孩的父母把女孩嫁给了这个神职人员。女孩被强迫结婚,在10岁时生下第一个孩子。)
“噢~,我要来了,主人,快点!我要来了。”客厅里娈童喊道。
“别扫兴,尤文提,放荡会让人无趣。”诗人说。
“慢点!主人,我受不了了,别肏了,别肏了!”
“我肏,我肏你这个淫荡的小屁眼。”诗人加快了动作。
“别肏了!主人,我要坏了。”
“我肏!我肏!我要把精液注入你的身体里,你是我的。”诗人肏得更得劲了。
一阵快速地冲刺后,他们俩趴在桌子上喘息。
卡米拉舔了一会没力气了,维修斯就抓着她的头发肏嘴,直至射精在她嘴里。
======
卡图卢斯在肏尤文提时,把尤文提想象成了维修斯。
因为维修斯居然对他说‘你于我无用’,这让他感受到了羞辱。
而更让他屈辱的是:他为了安全,要去巴结、讨好一个释奴(被释放自由的奴隶,也叫解放奴隶)。
这是他第一次和维修斯、卡米拉同住。
前几日卡米拉经期,流血本来就有血光之灾的意涵,经血更是代表着劳无所得,卡图卢斯当然不能和他们住,那太不吉利了。
今天眼见卡米拉不流血了,才和他们同住。
以他骑士的身份地位,本该他睡在卧室大床上的,却被维修斯抢了,当然他是因为对恩人的尊重没有抗议。
Visius是一个典型的角斗士名字,词根 Vis 意为暴力。
据传是一位居住在西西里的退役维斯塔祭司,把一个辛布里奴隶收为养子,并进行造神,说是日耳曼的雷神索尔降世。
意大利人为了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纷纷把辛布里奴隶都改名为维修斯,把这个名字奴隶化。
这个维修斯看起来20岁,也就是说辛布里战争时,他应该还是个孩子。
从他强健的身体,会弹琴、识字,可以推断他应该是个受宠爱的贵族家奴隶。
他高大的身躯,强健的肌肉,想来西西里那位维修斯也不过如此。只是,传说中的维修斯如阿喀琉斯般刀枪不入,这个维修斯是会受伤的凡人。
卡图卢斯从第一次见到卡米拉,就是知道她出生贵族,因为她识字、自信,还有手指上用发丝缠绕的露出一抹金色的戒指,只有贵族成员才能佩戴金戒指。
而且他们不经意说漏嘴,透漏了她的真名——卡米拉。
也就是说她是贵族卡米利乌斯家族的女儿!
她自称维西亚,就是把自己降格为奴隶的女人了,恬不知耻!
他们看起来像奴隶拐骗了女主人私奔,却不是逃去行省不被找到的地方生活,而是慢悠悠地来到罗马。
卡图卢斯得出一个惊人的假设:没有人在追赶他们!卡米利乌斯家族的男人们,可能已经死了!
从维修斯独自杀掉一群山匪来看,他有这个能力。
那么卡米拉就和美狄亚一般,是个为了爱情可以谋害父兄的可怖女人。
骑士和贵族的差异只是财富的多寡,都是经过数代人的积累才能实现的地位。
对于平民、解放奴隶通过歪门邪道,篡夺别人数代累计的成果,卡图卢斯是十分厌恶的。
本来他应该住进父亲的老战友的家里,在引荐下,用贿赂获得财务官的职位。做两年财务官后,再谋求更高的职位。
可是父亲的朋友死在内战中了,让这一切都成为泡影,他得重新打算,并且,他的人身安全需要得到保障。
维修斯已经成功上位了,而且,卡图卢斯必须得承认,维修斯是有其硬实力的。
然而,维修斯似乎还没准备好过一个体面人的生活,他对卡米拉很溺爱,这或许就是卡米拉这么爱他的原因,但他俩的行为都与其地位不相符。
维修斯不该让卡米拉骑在他身上,尤其是在她流着经血的时候,这种行为只适合奴隶和女主人,而夫妻做这种事,是妻子在羞辱丈夫的尊严,是丈夫在宣告妻子的无知、跋扈,这看似甜蜜的事却让他们俩人都受害。
只是他俩都还不知道,一个年幼,一个无知。
卡图卢斯觉得自己应该纠正维修斯,让他的言行与他新的地位相符,这是一个正直的朋友应有的劝告。
在小床上抱着尤文提,抚摸着他的小阴囊,卡图卢斯进行着睡前的胡思乱想。
不知何时入睡的。
因为罗马的街道十分的拥挤,白天禁止车辆进城,夜里就是送补物质的车辆进城的时间。
车夫的吆喝声、牛马的蹄子声、车轴的呻吟声,让他睡得很不安稳。
迷迷糊糊中他做了个梦,梦里他看到一只狼在啃死一具女尸,就是从土匪山寨跑出去,死在路边的那具女尸。
狼发现了他,用残暴的眼睛盯着他。
当他转身逃跑时,狼向他冲过来,他就被吓醒了。
梦境可能包对未来的预兆,他很清楚什么样的梦有预示未来的作用。他离家时带着祖传书籍《梦的解析》的抄本。
在梦中看见狼代表着损失,预示他可能要损失一些东西。
而女尸和他的关联是同样从山寨逃出来。
这说明,很可能他要损失的是从山寨带出来的东西。
钱袋!他立马想到,也有可能是尤文提,或是钱袋和尤文提。
从窗户缝里里穿进来的光线可知,天已经亮了。他推醒了尤文提,下床打开窗,让光线照进来,他去打开柜子查看钱袋,钱完好无缺。
当然不可能是维修斯、卡米拉抢夺他的财产,这俩人表现出对金钱的漠视,仿佛金钱是可以随处捡到的石头。
损失一定来自于外面。
“尤文提。”
“主人?”
“我做了个不吉利的梦,我可能会遭遇财产的损失,你今天不要出门了,呆在室内,确保安全。”
“是,主人。”
他在夜壶里尿尿后,让尤文提去把尿壶倒了,自己拿了钱出门买面包去了。
======
罗马人,通常是指占人口总数不到5‰的罗马精英阶级,另外那99.5%的人口是被忽略的。
就像中国说的秦朝人、汉朝人,实际上是指那个年代的士绅阶级,占总数大部分的泥腿子们,只以某年某事死了多少人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书籍里。
维修斯来到罗马15年,先是跟着马尼亚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然后去了西西里。
因为家人被屠杀的经历,索菲亚对于士绅、贵族有着明显的敌意。
贵族、豪绅不敢踏足阿格里真托,大农庄被分割城小农庄,小农、工匠受到庇护。
她坚持禁止给奴隶上镣铐,使得阿格里真托人对购买奴隶兴趣寥寥。
阿格里真托社会原子化,阶级矛盾不显着,不是真正的罗马城市。
当初在阿格里真托站稳脚跟之后,他释放了一批奴隶。
后来奴隶们住的宿舍楼造好了,每个小家庭分一间,那些离开的释奴后悔莫及。
有些人还试图再回来做奴隶。
这个时代的人对生存条件的追求,高于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只要能过得下去,奴隶逃跑并不是主流。
他到罗马来旅游,除了要看看罗马的建筑,也是要看看罗马市民的生活。
至于罗马贵族们的生活就没啥好看的,无非是剥削、奢侈、炫耀、联姻、倾轧和淫乱。
他来到这里,就是要看那些电视剧上不拍的、历史书上不写的——沉没在历史中的大多数人。
早餐后,他和卡米拉去公厕拉屎,公厕的石板上都是湿漉漉的,很难说清是什么液体造成,而且被称作维纳斯病的淋病挺常见的。
他不可能和罗马人那样,缠腰布一脱,毫无心理障碍地坐上去。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的公厕是不分男女的,他们的长袍在上公厕时可以很好的遮羞。
而习惯穿裤子和短上衣的北方民族,脱掉缠腰布则会暴露出生殖器,这是罗马人嘲笑穿裤子的日耳曼人、高卢人的原因之一。
维修斯拉屎是凭腿力蹲着的,而卡米拉拉屎时他用双手拖着她的屁股,不让她坐在有湿漉漉的石板上。
到达罗马的第二天,他已经开始怀念阿格里真托的舒适生活,尤其是他让陶匠制作的抽水马桶。
“哼~”一个秃头男人倨傲地哼一声,他的奴隶用一张有洞的皮垫铺在洞口,钻进他的袍子里解缠腰布。
秃头男人抬起头用鼻孔瞧人,坐在皮垫上,开始拉屎。
有一个妇人拎着便桶进入厕所,把尿粪倒入池中。
维修斯看了,决得也要买个便桶,就不用来公厕里拉。
“我好了。”卡米拉说。
维修斯用沾湿的麻布给她擦了屁眼,抱出公厕后,把她扛在肩上。
“维修斯,你为何不给卡米拉租一个轿子呢?她出身高贵,应当有符合身份的出行方式,骑在你肩上对她是坏事。”阴魂不散的诗人跟上来说。
“怎么是坏事?”
“得体的妻子当然不能像驾驭牛马一般骑在丈夫身上,你对她的宠爱会害了她的荣誉,也会伤害你自己的荣誉。”
卡米拉没有插嘴,但在他肩上侧着身子,八成没给诗人好脸色,如果手上有矛的话,可能要把诗人戳个洞。
“别跟着我们,诗人,你应该去竞选财务官。”
“我的担保人死了,今年不可能了,我得找个谋生的方法。”
“那就写点诗去卖,别跟着我们了。”
“我也打算往那边走而已。”
罗马城有个其他城市没有的特点,那就是室内比室外宽敞。
街上穿流不息的行人,就像两千年后中国国假时的旅游景点,拥挤不堪。
同时,高大的建筑内部却让人觉得很宽敞。
他们进入一座巴西利卡(Basilica),巴西利卡就是很多高大柱子顶着屋顶的开放空间。
靠路边的台阶上,坐着很多身边放着工具、胸口挂着木牌的男人。
走近看那些牌子,写着:木匠、陶匠、瓦匠、皮匠、玻璃匠等等,看来是些等着做日工的人。
罗马城的就业不足啊。
听到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维修斯往里面走。卡米拉从他肩上爬下来,握着他的手一起走,看来诗人的话对她是有影响的。
“你不必在意别人的话,我乐意扛着我的小宝贝。”他对她说。
她对他甜甜一笑。
往里走看到哭声的来源,是老师和学生们在一个角落里上课,一个笨孩子被老师拔了裤子用棍子打屁股,其他孩子幸灾乐祸地瞧着。
这座巴西利卡顶上最高处有十几米高,很高大,但也同样嘈杂。
有教授里拉琴的、双管笛的、画画的、雕刻的、跳舞的,挤在一起却能互不影响、各干各的。
值得一提的是:学跳舞的都是男孩,罗马人认为女人卖弄身体地跳舞是放荡的行为,体面的女人不准跳舞,只有妓女、演员这种下贱的女人才能跳舞。
舞蹈是属于男人的,用于展示阳刚和雄壮。
离开教授和学习的区域,看到有很多摆摊的人:看病的、卖魔法药水的、占卜的、看手相的、解梦的、卖书的,等等。
一个摆着很多瓶瓶罐罐的希腊老医生摊位前,有一个消瘦的病人,病人骨瘦嶙峋地躺在大理石地上,全身的皮肤上布满大小不一的囊肿,眼睑水肿。
希腊医生按压、揉搓着一个个囊肿。
“你确定你没有吃和其它奴隶不同的食物?如果你欺瞒医生,你的病也会欺瞒你。”
“好吧,我说。主人每次差我去采买,猪肉、羊肉、河鱼、海鱼,往回走的路上我会撕一些尝尝,这是替主人试试是否新鲜,也不是大罪过啊。除此以外,我和其它奴隶吃的都一样啊。”
“你犯了贪食的过错,神降下同样贪吃的虫子在你身体里,这些肿块就是虫子。”
“啊?!”病人吓得竖起来,惊叫道:“我找你看病,你可不能为了钱财坑骗我这个老奴隶啊!!”
病人的惊叫声引来更多的人围观。
“如果我坑骗你,就叫法官把我捉去关,或者叫朱庇特(宙斯)的闪电劈死我。我年轻时在埃及学医,在制作木乃伊的地方学习手术,我见过几个和你一样的贪食病,割开每一个肿块,里面都有虫子。”
“哎呀!!怎么治?医生,怎么治我呀?”病人哭嚎着。
“你先给我说好的诊断费1枚银币。”
“给你,给你,快告诉我,是要把这些肿块都割开吗?太多了!这太多了!”病人拍打着胸口的囊肿叫着。
希腊老医生收了钱,拄着雕刻有蛇的手杖站起来,有点防备姿态地说:“没法治。”
“没法治?”病人惊愕地看着医生,“你收了我的钱,就告诉我没法治?”
病人伸手要掐架时,医生娴熟地用手杖敲在病人的头上,“就是没法治!神降下的责罚,医生有什么办法治?不光是皮肤里,你的肌肉里、胸腔里、腹腔里都有虫子,祷告,只有向神祷告可以救你。”
“向哪个神祷告?”
“你是奴隶,家庭事务归朱诺(赫拉)管,去向朱诺祷告,快去。”
“噢。”病人向外跑去。
“还有谁要看病?”
吃瓜群众像是怕染病一般做鸟兽散。
维修斯发现诗人停留在一个解梦的摊位前,他也走过去瞧一瞧。
“我昨晚梦到我右边上面的臼齿掉了,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拉丁男人问解梦人。
“这说明你的父亲要死了,如果是梦到左边的臼齿掉了,就说明你母亲要死了。”
“你胡说,我父亲已经死了多年了。”
“显然,你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解梦人手一摊回答道。
“胡言乱语,上颌的牙齿确实代表长辈,梦见掉牙齿却不一定代表活人将死。”诗人骂道。
“你是哪里来的狗?”解梦人站起来骂道。
维修斯赶紧抱起卡米拉跑出了巴西利卡,摆脱了跟屁虫。
“用你们的眼睛去看,街上路人的脓包、疱疹、溃疡是不是越来越多了?这是阿波罗(太阳神兼职掌管瘟疫)的惩罚!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克拉苏的过错!你们听我说。”
“听他说!”人群里有人帮腔。
他们走出巴西利卡的另一头,看见一个拉丁人在高声演讲。
“你们在外面可能是别人的工匠、附庸、雇员,但在家里,你们是自己家庭的国王,你们的母亲、妻子、女儿是你们的财产。而大富豪克拉苏,他已经如此的富有,却还要把手伸进你们的家里,他凿开了一条恶之河。你们听我说。”
“听他说!”
“克拉苏他在宴会上以亲吻权之名,亲了附庸的妻子和女儿,他滥用了不属于他的权力。别走,也许你觉得和你们无关,听我说,你们马上要遭殃了。”
“别走,听他说!”
“克拉苏附庸们的妻子、女儿被亲了嘴,他们不敢报复克拉苏,却敢把羞愧的怒火撒在你们身上。他们去自己的附庸家里,那些和你们一样的商贩、工匠家里,强行亲吻他人的妻女。还有克拉苏的朋友们也在效仿,如果你们不联合起来反抗克拉苏,用不了多久,你们的妻女就会被别人搂在怀里亲嘴了。他们会带给你们的妻女无尽的痛苦,带给你们永远无法抹除的羞耻和疾病。”
“闪开!滚!”几个手持盾牌木棒的打手包围上去。听众们哗哗做鸟兽散,演讲的人拔腿向巴西利卡里面往逃跑,打手们追进去。
维修斯扛起卡米拉,往街道更整洁的山上走去。